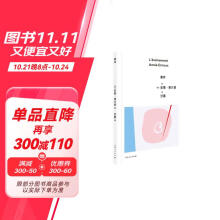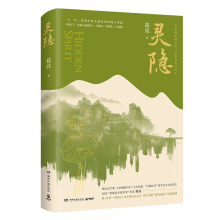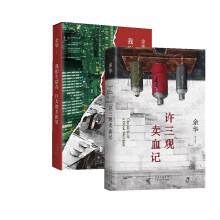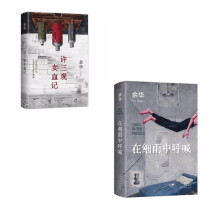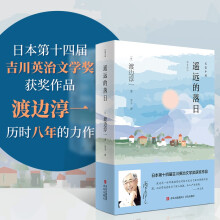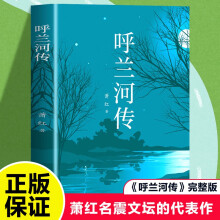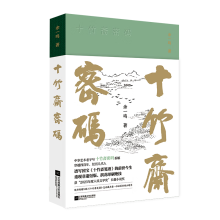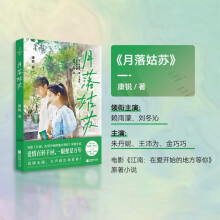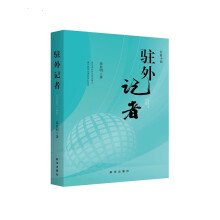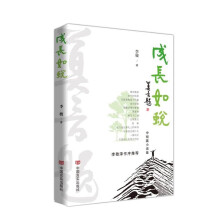一
关于父亲和母亲
人的生命的每时每刻也许都在时间里沉淀。当然,站在佛学的角度来说算是一种修为吧。
曾经有个地方有兰花烂漫之陵,却不知是何人之陵,如今已荒废许久。只有这片土地,独自瓢饮着曾经。宁静,这把钥匙,偶尔打开从前的从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需要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寸土地、每一滴水会偶尔打开这本无字天书,任时光随意流逝,在一缕清风里诉说着无人能懂的曾经。
土地是真正的主人,养育了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无数无量的生物和人类,它不需要被人所感恩、所记起,它无视你的存在,无视生死离别,在无数个生死交替的轮回中,土地不会记起你是其中的哪一粒尘埃。风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开始,因为在无数个年代以前就已经横扫于天地间,没有停过,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雨不知道什么是开始,因为在无数个年代以前就随性而发。冬去春来,这里的草木总是“偎依”在土地里,沐浴在阳光里,如果说人有轮回的话,我也不知道在诉说六道轮回中的哪一道,也许在茶余饭后的时候当作时间空白处的一个填充吧。
田昌军弟兄四五个,他最小。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正好赶上田昌军出生,后来他曾问过他父亲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他父亲慢条斯理地说:“为什么姓田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这个名字也是有意义的。我小的时候亲眼见到大清国的官兵,后来又遇上国民党的官兵,又见到了这新中国的官兵,看见那种排山倒海的阵势,才知道咱一个小老百姓连一只小蚂蚁也不如啊。”
田昌军并不懂这些,在他父亲眼里,军人是一种强悍和征服。
转眼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了大炼钢铁和高产增产的年代,那个时候生产队里有人推算过,说是一亩地种上十几斤麦种就可以收获几百斤粮食,要是一亩地种上几十斤,几百斤,几千斤麦种的话,哪怕是一粒种子的麦穗上结三五粒儿,那不就是亩产几千斤?上万斤?于是,那年种小麦的时候生产队下了死命令,把仓库里所有的小麦都撒到地里,就连地里的红薯也不能收获人仓,要把它深埋在地里,期待来年能有更大的丰收,争创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纪录。但是极度的寒冷早已把地里的红薯冻坏了,烂成一摊稀泥。地里的麦苗更是长得一塌糊涂,队长看在眼里实在是着急,最后没有办法了,只得隐瞒了上级,连夜找人把麦苗拔掉一大半,总算是保住了一亩地正常的产量。记得一次田昌军饿得实在是不行了,从墙角里找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着蒸馒头用的面引子,在锅里煮着。那个年代各家刚刚实行公社所有制,私人是不能烧火开灶的。青烟升起,没大会儿,引来了生产队长。队长姓万,田昌军喊她嫂子,她坐在门槛上不说话,一直看着火焰和熏黑了的铸铁锅。田昌军打开木盖子,一股酸味儿从锅里飘出来,队长看到黑不溜秋的一块被虫蛀了的面引子出现在锅里,这才悄然离开。
阴霾的日子过去了,田昌军走进了学堂,教他的老师姓杨,腿有点儿瘸,孩子们背地都叫他瘸子老师。那年夏天,天气非常热,中午吃饭的时候田昌军干脆就把书包挂在池塘边上的小树上,自己跳到池塘里洗澡、逮鱼去了。不巧,那瘸腿杨老师正好路过,于是他不出声地坐下来,在池塘边上的老榆树底下看着池塘里的小家伙儿。
田昌军喜欢抓鱼在小伙伴里是出了名的,看到老师在岸上瞅着自己,于是就朝岸上扔来几条乱蹦乱跳的鲫鱼。老师坐在树底下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道:“田昌军啊,你说你要是把捉鱼的兴趣和本事放到学习上那有多好啊。”
“老师,你说的那些没有用,那些语文书上的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再说你教我的算术也没有什么用,你说咱队里的粮食谁会一粒儿一粒儿地数?咱炒菜的辣椒谁能说标准的一盘子菜放几个?你说筷子到底是两根还是一双?还是这个鱼来得快。在这水塘里又凉快又有鱼吃,不管是白水煮还是烧火烤,它都比上学管用啊。”由于天太热了,田昌军在水里实在不想上岸,笑嘻嘻地和老师狡辩。
“唉,你这孩子啊。”老师看着水里的田昌军,无奈地离开了。
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田昌军已经长成了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虽然经历了闹饥荒的年代,但是他长得还是清秀、阳光,破旧的衣服并没有遮盖他眼神里的锐气。
又到收麦时,那“麦浪滚滚闪金光”的歌声到处弥漫,生产队里的男人和女人分成两伙儿,分别从麦地的两头往中间收割。流言蜚语有时候能把假的变成真的,也能把真的变成假的,无中能生有,有的东西也能被流言蜚语摧毁。那一次的经历成了田昌军心里的一道疤。
快收工的时候,生产队长还是没有招呼大家收工吃饭,一天的劳累早已让大家没有了劳作的力气,田昌军肚子早已经咕咕叫了,无奈只得把那一罐子冷开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个足。就在他刚放下茶罐子的时候,听见队长在远处招呼大家:“收工回去吃饭啦……”大家听到“收工”,连忙拿好各自的镰刀,巴不得一步跨到公社食堂饱餐一顿。田昌军听到了生产队长的叫喊声,一下子尿急。
P1-2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