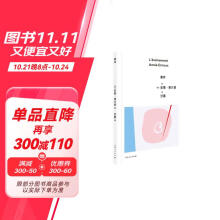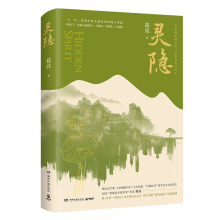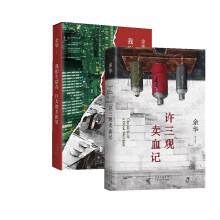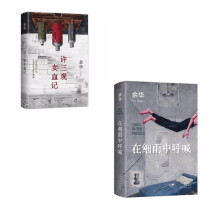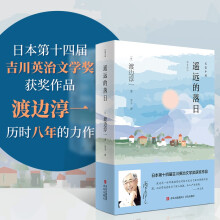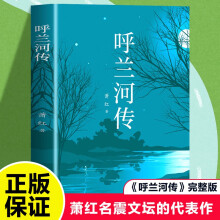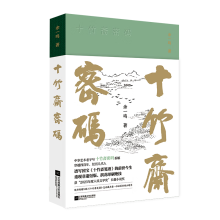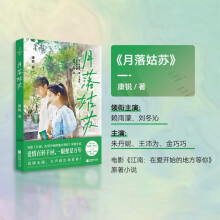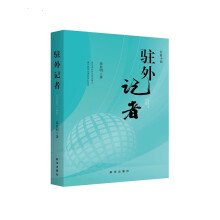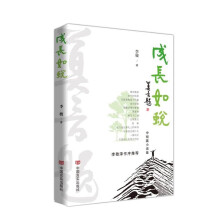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只有香如故》:
楔子
探寻 穿越
岁月无声,转瞬很多年过去了。记忆中,梅花山古窑厂(梅花窑)几乎一直保持着低矮一片的窑工作坊。那碎陶片、石子、泥土混杂的道路,土砖、土墙,还有用豆腐乳坛子砌就的房子及院落,似乎就在眼前。古窑厂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已然逝去,留下的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或许岁月老去了它的身子,但无法腐朽它的灵魂。古窑厂成就了一段段厚重的人文历史,那大缸、小缸以及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里盛满着多少窑工的故事,留下了多少凄美的传说……
梅花山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西十里处,偏大工山东麓,是一座不起眼却别具一格的小山。每到冬季,这里漫山遍野的梅花飘香,犹如人间仙境,让人沉浸在幸福温馨里。梅花山古窑厂煅烧出的陶器,早在同治年间就在四乡八野很火,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远销东北三省,每每出一批窑货总是被抢购一空。
母亲在梅花山古窑厂的老宅住了60多年,直到2003年父亲离世,母亲才离开老宅与子女们一起居住。老宅就要被拆了,2011年10月,我和姐妹们陪同年迈的母亲去老宅看看。
抵达老宅,记忆中用毛竹编制的两扇院子大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用陶器瓦罐、豆腐乳坛子围起的院墙,也早已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敞开着的、无人看管的院落。被一大片一人多高的蒿草围住的老宅,空落落地端坐在那里,此刻更显寂寞沧桑。一丝愁绪涌上心头。一切都在变,原先热闹的家园、鸟语花香的院子,已然一片荒凉。曾经的繁华景象,早已成了过眼云烟。
白发苍苍的母亲像一个指挥官,急切地指挥堂哥袁从洲拿来镰刀砍去一些蒿草。很快,一条窄窄的通往家门的小道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抓着相机到处拍,拍完老宅,再去拍摄已经被岁月风化了的古窑,生怕这一丝古迹马上就要消失了似的。
老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还是爹爹(爷爷)、奶奶创下的基业,土墙、瓦盖,白色的石灰墙虽已斑驳发黄,但还像山一般稳稳地立在那里。一把锈迹斑斑、锁住童年记忆的大锁,从洲哥哥费了好半天的力气才打开。
小时候觉得这个家很大,一排房屋共有十几间。房屋里曾住着爹爹、奶奶和他们的儿孙们。树大分枝,后来大伯袁美琪和三叔袁少明一家搬到五里陶瓷厂,这里就留下小叔袁少信和我们一家。那会儿这还算是大户人家房舍,现在怎么也看不出当年的恢宏气势了。
母亲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满脸忧郁地站在大门口愣神,毕竟这是她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妈,我给你与老宅拍一张合照留念吧。”母亲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挺了挺已经微躬的腰,一脸严肃地站在老宅前。我迅速地连拍,相机镜头里瞬间出现了魔幻般的情景。我看到了母亲年轻时漂亮的容颜和幼年时的自己。小时候在庭院里纳凉的景象,一幕幕地在镜头里浮现……
几个小姐妹躺在两张并拢在一起的竹床上,伯伯(湖北地方称父亲为伯伯)和母亲分别坐在竹床的两边,用芭蕉扇给孩子们扇着风,时不时地赶着蚊子。哥哥紧靠在父亲的身旁坐着,手执一把折叠扇扇着风。
我家有八兄妹,哥哥袁从新是家中的老大,也是唯一的男孩。言语不多的哥哥突然说:“伯伯,今晚再给我们讲几个故事好不好?”伯伯端起旁边凳子上的茶水喝了一口,说:“细伢们(湖北地方对孩子的称呼),你们要不要听啊?”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嚷着:“伯伯,要听、要听。”伯伯可是个讲故事高手,这也是他最能镇得住孩子们的法宝。孩子们不再为躺在竹床上你挤我,我挤你而吵闹了,常常在故事中迷迷糊糊地睡去。
此刻我有些莫名的感觉,伯伯袁少棠很受当地人的尊敬与爱戴,人称二爷,已经辞世十几年,难道这世上真的有穿越?我还在愣神,似乎又听到伯伯在说话:“红儿,怎么坐起来了,你在发什么杲呢?好好躺着,我给你们说说梅花窑的故事。”父亲饶有兴致地说起梅花山陶瓷厂的由来。
“南陵县西,蜿蜒起伏的七座山岭重嶂叠翠,景色秀美,古时有七朵梅花之称。梅花山陶瓷厂地处南陵县西十二里的地方,占有三朵梅花,故名梅花山陶瓷厂。
“要说起这梅花山陶瓷厂,它最早的名字叫梅花窑。一百多年前,一群湖北手艺人逃荒来到这里,搭棚为屋,挖地为灶。他们站稳脚跟后,研究土质,寻找陶土,勘察地形,纷纷建窑。他们自己动手制作陶车,生产陶坯,烧制陶器,后来都过上了安逸的生活。梅花窑里流传着很多带有传奇色彩的凄美故事……”
小妹们早已习惯了听故事入眠,发出均匀的酣睡声。只有大姐、二姐和我睁大好奇的眼睛,生怕错过后面精彩的片段。大姐性子急,追问了一句:“那后面的故事呢?”伯伯说:“霞儿,不早了,你小妹们都睡着了。梅花窑的故事有趣得很,还长着呢,我以后再慢慢说给你们听。”后来,关于梅花窑的前尘往事,父亲一直说了很多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