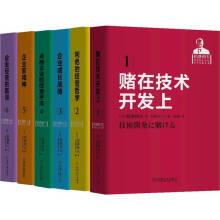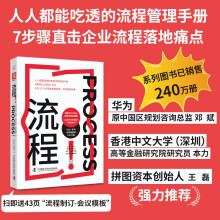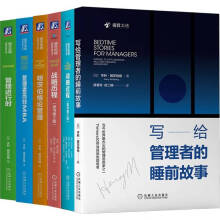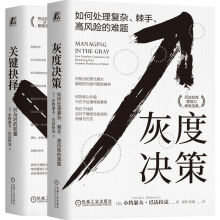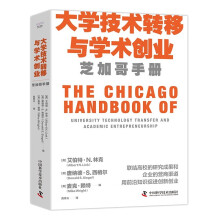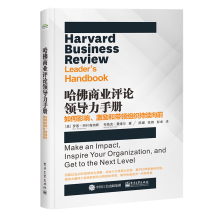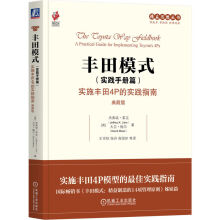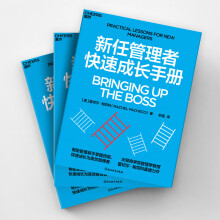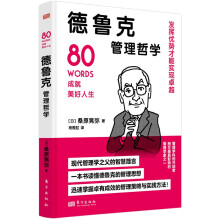当两个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原始部落发生竞争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基础上,拥有众多勇敢、富有同情心、忠诚的成员的部落将具备优势。这些成员在面临危险时始终会互相提醒、互相支持、互相守护。在这场竞争中,这个部落将战胜对手并征服另一部落。——摘自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1871年)利他(Altruism)一词英文的词源为拉丁文Alter,意为“他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利他的定义。例如,Batson等(1995)从利他的结果出发,认为利他的核心在于增加他人的福利;Post等(2002)则更强调利他的动机,认为利他应该是真正为他人的利益或幸福着想,而不是作为利己的手段;Organ(1988)的定义侧重点在于利他行为对自我利益的牺牲,认为利他指的是个体对其他个体进行帮助的动机及行为,即使这种帮助可能造成自身利益损失;Oliner等(2002)的观点则更为综合,认为利他有四个条件,即目的在于增进他人的利益或幸福、利他者面临风险或利益牺牲、没有外部来源的回报以及利他者的自愿性。上述学者们对利他的定义中潜藏了一个认识,即关于利他的讨论分为两个层次:指向他人的无私行为及行为背后的心理特征(Vlerick,2021)。
利他一直是生物学特别是社会生物学的重点概念。这个领域中的学者们关注的是利他行为背后的演化机制,即为什么在生存是自然选择主要动力的前提下,个体还愿意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资源或利益去帮助他人(Kohn,1990)。根据上述关于利他的行为与心理二元区分,利他可以分为心理利他(Psychological altruism)和生物利他(Biological altruism)两个层面。其中,心理利他只关注利他的心理动机,即个体想要通过自己的付出而让其他个体获益的愿望。例如,Piccinini和Schulz(2018)提出了两种心理利他的机制,一种称为传统心理利他(Classical psychological altruism),这种心理利他的终极驱动力是利他需求,会让个体产生为了受助个体的利益而帮助受助个体的行为;另一种则称为非传统心理利他(Non-classical psychological altruism),这种心理利他的终极驱动力是利己需求,会让个体产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他的行为。而生物利他,也称为演化利他,则只关注利他的行为表现,即个体做出提升他人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适应性(Fitness,即生存和繁衍的机会)但相应地降低自身适应性的行为(Vlerick,2021)。简而言之,想要帮助其他个体的愿望是心理利他,而实际帮助其他个体的行为则是生物利他。
演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长期以来是解释利他特别是生物利他的主要理论之一。具体地,演化论对利他行为的解释一般聚焦于两个领域。一个领域试图给出个体帮助有亲缘关系的其他个体的动力机制,其核心概念为亲缘利他;另一个领域则试图给出个体帮助与其毫无血缘关系的其他个体的动力机制,其核心概念为互惠利他(Vlerick,2021)。所谓亲缘利他,指的是个体对与其共享同样遗传基因、存在血缘关系的其他个体的利他行为。演化论认为,亲缘利他是由预设在个体基因中的一种基础生理动力所驱动的,目的是确保与个体共享同样基因的其他个体有更好的生存与繁衍的机会(Darlington,1978)。亲缘利他的逻辑比较明了,针对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个体的利他行为将有利于提升共享遗传基因的亲属的适应性,从而提高他们所共享的基因的演化成功率。因此,亲缘利他行为的基因编码在有亲缘关系的个体间很容易传递,从而得以广泛传播。除亲缘利他外,个体的利他行为还会扩展到与其并无血缘关系的其他个体身上。互惠利他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Trivers(1971)提出,即使没有血缘关系、并不共享共同的基因的个体之间也可以通过相互帮助而让彼此受惠,从而同时增加互助双方的适应性和演化成功率。
但是也要看到,人类社会中有些行为很难用基因的适应性和演化成功率理论来解释。例如个体对毫无血缘关系的他人的帮助,往往带有对自身资源或者利益的牺牲(Organ,1988)。这类行为并不适用于亲缘利他或互惠利他的原理。面对这类问题,Vlerick(2021)提出了基因-文化群体选择说,认为文化群体选择与基因群体选择一样,是个体和群体生存与繁衍的重要机制。演化过程不仅塑造了个体的基因,也塑造了人类文化的特征。文化通过“扬善惩恶”,让人类可以实现“自我驯化”,在基因特质上越来越亲社会。这种文化演化影响基因演化的过程也称为“基因-文化协同演化”,即文化上不断演化的社会环境“操纵”了人类在基因层面上的演化。通过基因与文化的协同演化,人类变得越来越利他。
的确,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社会性表征,在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体所组成的组织中普遍存在着成员之间的利他行为。如Smith等(1983)所言,每个工厂、公司或者办公室,日常都离不开成员之间的互相合作及互帮互助。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与组织架构的日趋扁平,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组织必须给予成员更多自由决策和行动的空间,才有可能让其更灵活地处理日益复杂的工作需求,从而帮助组织更好地生存和发展(Shalley et al.,2009)。同样,对于个人来说,要想更好地在当前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中适应和发展,也需要经常做出超越本身职责的工作行为(Eissa et al.,2019)。因而,包括利他在内的组织内个体角色外行为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组织中利他的价值也得到了学术研究的支持。研究者们发现,以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为代表的组织内利他行为对包括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职业成功、组织效能在内的个人与组织结果都有重要影响(e.g.,Griep et al.,2021;Halbesleben et al.,2010;Munyon et al.,2010;Russo et al.,2014;Singh & Singh,2019;Yaakobi & Weisberg,2020)。
虽然利他对于组织如此重要,但是当前关于利他的研究,在对其本质特征的认知、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问题。第一,此领域内的研究者长期以来都假定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Bateman & Organ,1983)。这些人被称为“好公民”(Good citizens)或“好士兵”(Good soldiers),他们身上的一些特质让他们稳定不变地做出利他行为。换句话说,学者们普遍认为,利他行为等角色外行为是特质性的、静态的,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个体之间(Bolino et al.,2012)。基于这个理论前提,绝大多数的利他行为或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都聚焦于对利他行为静态点值的个体差异前因进行探索(Bergeron,2007)。然而,这个理论前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近期研究逐渐显示,这些角色外行为的水平在个体内并不是绝对不变的(Dalal et al.,2014),而是“进行中的、动态的和依赖于时间的”,体现出个体内的变异(Bolino et al.,2012)。围绕利他行为的动态性特征,一些学者开展了初步的探索,并发现利他行为同时存在着短期的波动性变化(Lowery et al.,2020;Smith et al.,2020)和长期的趋势性变化(Lin et al.,2020;Parke et al.,2020;Yu et al.,2017)。总体来说,新近研究显示,利他行为对组织中的个体来说并非静止不变的行为,而是不管在短期波动上还是长期趋势上来说,都属于存在较大变化可能的动态行为。
第二,基于对利他行为动态性的认知来重新审视Organ(1988a)等学者对于利他行为的经典研究,可以看出,早期学者们定义的能够推动组织效能的持续稳定的利他行为(Methot et al.,2017),其实是利他行为的理想化状态,即短期波动性较小、长期趋势平稳(甚至上升)的“可持续”利他行为。由于与工作绩效等具有标准要求的工作行为不同,利他行为是工作职责以外的随意自愿的行为(Bateman & Organ,1983),并无特定的标准与要求,其动态性变异可能比其他工作行为更加显著。因此,在组织中可能实际存在着短期波动性较大、长期趋势下降的不可持续的利他行为。然而,先前大多数研究对利他行为的考察中,在某一时间点取样的利他行为的单次点值或个体知觉到的一段时间内的均值(频率),不仅无法反映利他行为的长期趋势特征,还掩盖了利他行为短期波动中可能出现的异常值,从而可能导致将不可持续的利他行为误判为稳定持续的理想利他行为,给组织带来严重恶果。例如,将利他行为短期波动的极高或极低水平的异常值误判为均值或稳定值,会造成对员工利他水平的过度高估或低估,导致后续绩效考核、福利激励、岗位配置的一系列错误决策。而对团队成员利他行为长期下行趋势的失察,可能导致无法发现组织中存在的制度、政策、人员安排等方面的严重隐患。因此,为了准确客观地了解组织中利他行为的特征,动态地对其包括短期波动性和长期趋势性在内的可持续性特征的考察是极其必要的。
第三,当前已有的对利他行为的动态性考察,在系统性上存在着明显不足。当前以动态视角对利他行为进行探讨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从时间框架上可以分为两类,即短期研究和长期研究。短期研究一般采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s),探索利他行为及组织公民行为在每天甚至分钟级别的波动性(Glomb et al.,2011;Lowery et al.,2020;Smith et al.,2020;聂琦等人,2021)。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组织成员来说,在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内其组织公民行为有高达22%~87%的变化幅度。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利他行为在较短的时间内会呈现出动态性特征,产生短期(分钟、小时、天)波动性。长期研究则多采用多次纵向追踪调查(Longitudinal study),探索利他行为在月、季度甚至更大的时间框架下的长期变化趋势(Methot et al.,2017)。例如,有学者发现一些员工的利他行为在长期趋势上是下降的(Lin et al.,2020;Yu et al.,2017);还有研究者通过进行组织干预,发现了员工的利他行为在月级别上的上升趋势(Parke et al.,2020)。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涉及利他行为动态性研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利他行为同时具有长期的趋势性和短期的波动性(Methot et al.,2017),但已有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不同的研究框架、研究手段和研究样本,对利他行为的波动性和趋势性各自独立进行探讨。这种将利他行为动态性特征割裂开来探索的结果就是,研究仍然无法回答以下问题:利他行为的短期波动性和长期趋势性是否有内在联系?如果有,它们的互动机制又是怎样?如何完整反映利他行为动态性特征的全貌?利他行为动态性特征的全貌如何?在一个研究框架中用同一样本对其短期波动性和长期趋势性及其关系机制同时进行考察是极其必要的。
上述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会导致一系列连带的不良后果。首先,对利他行为可持续性特征探讨的缺失,会导致对利他行为何以产生即其机制研究同样存在片面性。例如,先前研究在探讨利他行为的前因时,只以提升利他行为单点水平的因素作为有效前因。例如,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英雄主义动机可以提升个体的利他行为水平(Franco et al.,2011)。然而,在加入时间因素,考虑利他行为的可持续性之后,可能原本被认为有效提升利他行为的因素,其实起到的是对利他行为初始水平提升但长期趋势下降、不可持续的效应。如果仅以单点利他行为的前因作为典型利他行为的前因,就会导致对利他行为前因的有偏,甚至是错误的认知,更会对实践领域产生错误甚至有危害的指导。相应地,只有将利他行为的动态性考虑在内,探索能够让个体持续产生利他行为的内外在条件,才能够真正发现对组织有价值的利他行为前因。其次,如前所述,以静态视角、单点测量的方式考察利他行为,还可能导致将不可持续的利他行为误判为稳定持续的理想利他行为,给组织带来严重恶果。因此,利他行为的可持续性特征对个体及团队、组织的结果的作用机制也亟须探究。因为利他行为最重要的特征是人际互动性,以动态视角看待利他行为的可持续性,不仅个体水平的利他行为可持续性对重要的个人结果的作用机制需要重新考察,而且团队与组织成员的可持续利他行为可能存在的互相影响机制也需要厘清。组织中成员的利他行为也可能呈现出一个在时间线上时刻彼此互相影响的形态,并共同构建起团队与组织可持续互利的图景。然而,对团队水平的互利可持续性如何影响团队有效性及重要个人结果的探讨也非常缺失。
总体而言,当前关于利他行为的研究,由于主要以静态视角采用单点横截面方式进行考察,在定义和测量方式上都更加侧重于利他行为的特质性,而对利他行为的动态性特征缺乏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证上的检验,会导致对利他行为特征的理解、利他行为的形成机制及其在个体和团队层面的作用机制上都存在偏误的可能。而近期初步出现的对利他行为动态性特征的探讨,无论是短期波动研究还是长期趋势研究,因为其研究框架与方法的割裂性,各自单独都无法完整反映出典型利他行为动态性特征的全貌。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组织中利他行为的可持续性,以动态视角,从利他行为的可持续性入手,在一个研究框架中用同一样本重新审视和考察利他行为的动态特征(包括短期波动性和长期趋势性)、形成机制和个体与组织层面的结果,对准确地回答什么才是可持续的利他行为、可持续利他行为如何实现、利他行为会给个人和组织带来什么结果等问题非常关键。因此,本研究基于动态视角,聚焦可持续利他行为的动态性特征,对其展开系统研究。
具体地,第一,本研究将回顾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这两个重要的组织中利他相关概念,其中前者是利他行为的典型代表,而后者则是利他行为的“对立面”,并对两个概念的关系机制进行探讨。
第二,本研究将以动态视角,重新审视利他行为可持续性特征,在统一的研究框架中研究利他行为的短期波动性和长期趋势性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与利他初始水平的关系,不仅对准确地回答“什么是可持续的利他行为”的问题非常关键,也为后续继续回答“可持续的利他行为如何实现”“可持续利他行为会给个人和组织带来什么结果”等重要问题奠定基础。
第三,本研究将对可持续利他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考察,探索个体因素与领导因素如何通过利他行为动机的中介影响利他行为的可持续性。仅以单点利他行为的前因作为典型利他行为的前因,会导致研究对利他行为前因的有偏甚至是错误的认知,更会对实践领域产生错误甚至有危害的指导。只有将利他行为的动态性考虑在内,探索能够让个体持续产生利他行为的内外在条件,才能够真正发现对组织有真正价值的利他行为前因。本研究考察个体因素、领导因素等对利他行为可持续性的影响,并探讨导致利他行为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的中介机制。
第四,本研究将更进一步探索团队水平的互利形态对重要的个体与组织结果的影响。以动态视角看待利他行为的可持续性后,组织中成员的利他行为会呈现出一个在时间线上时刻彼此互相影响的形态,并共同构建起团队与组织可持续互利的图景。然而,对团队水平的利他可持续性如何影响团队有效性及重要个人结果的探讨也非常缺失。本研究以多层分析视角,探索团队层面的可持续互利形态对重要的个体与团队结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可持续利他行为和可持续互利团队的作用机制模型。
上述研究成果不仅能够对利他行为研究做出显著的理论贡献,也对建设可持续互利团队与组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指导组织管理实践。构建具有利他文化的组织是很多组织管理者的理想之一,在组织中推进员工的利他行为、建设互利型团队也是很多组织正在开展的实践。本研究的成果不仅可以帮助各类组织的管理者增进对利他行为本质、形成及作用机制的了解,还可以基于研究结果帮助组织改善员工行为和工作绩效,构建高水平互利互助的团队及组织。研究成果同时还对我国增进全社会的利他氛围、形成高水平的互利文化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