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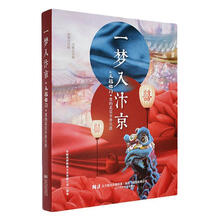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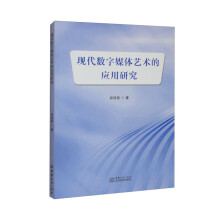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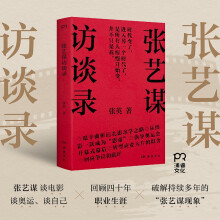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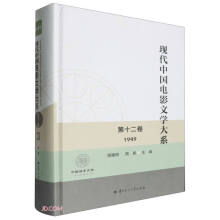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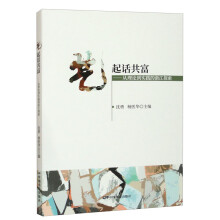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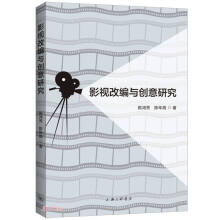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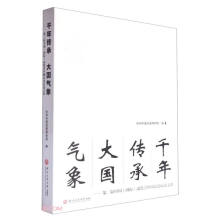

1, 从0到1:国内聚焦非洲电影的通俗作品;
2, 中国视角:电影学博士、纪录片导演张勇摈弃好莱坞非洲大片的叙事窠臼,以中国学者自己的视角,带读者透过影像重新理解非洲;
3, 多部经典影片解析:从《战狼2》《红海行动》《万里归途》,到《黑女孩》《刚果风云》《半轮红日》,解读几十部中非电影经典佳作;
4, 文化互通:以中国之非洲、非洲之非洲、非洲与世界为经纬,在中非交往日益密切的语境下,呈现中非文化的深层互动;
5, “理解文明”丛书之一:便携本设计,装帧精美,满足多样阅读需求,富典藏价值。
非洲作为一个遥远的大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乎不被认知,“60年代以前,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处于殖民地或被反共政权控制的状态,中国较少关注非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非洲作为第三世界阶级兄弟的概念被广泛普及,但普罗大众对非洲的认知也止步于政治框架中,遥远而抽象。中国人对于非洲更为具体的认知源于“文革” 结束后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门重启,电影交流逐步重新与国际接轨,从《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85)到《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1)、《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2004)、《血钻》(Blood Diamond,2006),中国观众在西方的空气里感受到非洲的味道,神秘、野性、血腥和暴力。浸淫在西方大片的影像世界里,我们跟随白人的非洲想象而想象非洲。
欧美电影长期垄断着非洲的美丽和外部对其的想象。到非洲拍片,首先是一个电影工业实力的体现。欧美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要,从殖民时代便开始拍摄非洲。当时,英国成立了“殖民电影委员会”来进行制片管理,拍摄了《桑德斯河》(Sanders of the River, 1935)、《所罗门王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 1937)等一系列殖民电影。结束政治殖民之后,文化殖民的梦魇并没有远离非洲。欧美电影人持续沉淀既有的书写非洲的模式,并随着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绎创新。他们拍摄出来的非洲影片,从情节设置到美学手段,都比非洲本土电影更具观赏性,直至今天仍在中国观众中影响巨大,并借助盗版碟和互联网深刻垄断了我们有关非洲的想象。
中国电影人去非洲拍片,首先,面对的难题是文化方面的障碍,绝大多数中国人“谈非洲色变”,遑论去非洲拍片,而一个摄制组则需要几百人甚至成千上万的人,克服文化偏见和心理障碍便成为首要的挑战;其次,创作者对非洲影视行业的几乎零认知成为赴非拍摄的现实困难,需要大量补在非洲进行影视拍摄涉及的拍摄许可、外景勘探、电力供应、器材设备(如大摇臂)以及政局稳定、疟疾危害、人身保险等等业务和常识功课;再次,是距离,相比欧美国家,中国距离非洲更遥远,由此带来的就是摄制组高昂的成本,当中国电影工业基础和市场不够强大时,去非洲拍电影无异于天方夜谭。这些心理或现实问题,对中国电影摄制组形成了巨大考验。
转折出现在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实力的整体增强,中国电影人频繁走出国门取景拍摄,美国、日本、泰国、印度及欧洲、中东、逐步被摄入中国银幕,在相关取景地引领旅游热潮之后,出现了不计其数的跟风之作。观众逐步对这些区域丧失了原初的新鲜感,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于是非洲这片广阔的处女地成为可供开发的新视域空间。市场需求之外,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政策的鼓励也驱动着中国摄制组走进非洲。2015年年底颁布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提出:向对方国家电视播出机构提供影视剧,探讨建立长期合作模式,继续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影视节展,积极开展纪录片、影视剧的联合制作;中方将鼓励非洲国家制作影视节目,加强交流并促进非洲影视作品进入中国。
《终极硬汉》(图11)成为第一部对这一计划进行回应的电影。该片故事背景设置在非洲图卡加这样一个虚构的地区。特种兵转业的韩锋的妻子三年前为了写作一部冒险小说带着孩子来到非洲,后不幸离奇失踪。韩锋从香港来到非洲寻找妻子的下落,然而在寻找过程中意外被卷入与国际军火走私团伙的斗争中,着力保护一个发现非洲超能量石而外貌形似妻子的女孩。影片由动作演员出身的陈天星自导自演,并“聚集15国动作影星联纵打造硬片”,场面设计融合了大量好莱坞和非洲的元素,飙车戏、爆破戏都以非洲的荒漠为背景,相较同类题材更加逼真。然而本片在后期宣传上出现不当行为,导演陈天星在上映前夕发布“金援王宝强”声明,称愿意拿出《终极硬汉》票房片方收入的5%支持王宝强打离婚官司,被指故意炒作,影片一上映便遭遇恶意低评、迅速下线,最终仅收获几百万元的票房。
笔者曾专门就此事采访过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加蓬籍演员、本片主演吕克·本扎(Luc Bendza)。
中国非洲题材首次试水便遭遇滑铁卢。
……
温馨提示:请使用员工书屋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