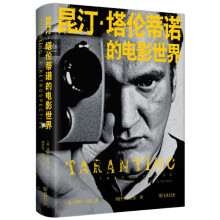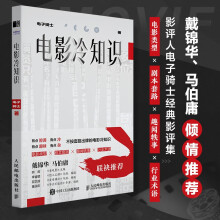《萧祖石作品选》:
月台上一个旅客也没有了。
我明明知道没有了希望,但我还是固执地循着一节节空寂的车厢,从头到尾,又找了个遍,仍不见表姐的影子。信上不是明明写着今天到达吗,难道她在西站下车?不会,慢车在那里不停,再说,她哪儿来的钱买快车票呢?是她写错了时间,还是突然有了什么别的变故?想到这里,我愈加不安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完全沉浸在苦乐参半的往事里。别看我们是表姐妹,却不亚于一母同胞。我每次到舅妈家,表姐不是把着手教我绣花,就是领我下湖划船,在荷花丛里捉迷藏。她时而在这里抛头,时而从那里露面,吓得那小鱼小虾乱窜乱跳,尤其是采莲的季节,下湖采莲,边采边吃,不是我嘴馋,莲籽肉又甜又嫩,好吃极啦。吃着,玩着,快活得什么都忘了,直到傍黑,不得不回家的时候,表姐才难舍难离地送我一程又一程。我还没到家,就扳着指头计算着下次来舅妈家和表姐见面的时间,难怪妈说我和表姐是两块糯米糍粑,成了堆,黏成块,刀都切不开。我十四岁那一年,和表姐在一个中学念书。她高一,我初一。我俩床挨床,头顶头睡觉,她像个小先生对我管得很严,督促我做作业,检查我的卫生,我又亲她,又有点怕她。表姐是学生会的干部,品学兼优。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号召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的表姐不声不响地在报名簿上第一个郑重地写上了她的名字——刘湘莲。当时,我也暗暗下了决心,等我高中毕业后,也要学表姐的样,到她那里安家落户。可没料到,我初中刚刚毕业,学校就动员我到省城上了中专,和我朝夕相处了三年的表姐分开了,我俩的眼圈都红了。我去省城上学的那天,表姐特意赶到车站,把一个小薄纸袋,塞进我的口袋里。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拆开一看,啊,是个绣得漂漂亮亮精致秀雅的桃形相夹。相夹里夹着我和表姐的合影照片,照片后面写着“姊妹情深似海”几个字。看看表姐那端端正正的字,又看看相片上表姐深情的眼神,我不由自主地把头伸向窗外,回头望望在月台上的表姐。火车已出站好远了,但我隐隐望见,表姐手里挥动的那块雪花似的手帕,依然飘扬在风里。
啊,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中专毕业后,留在省城当了技术员。听说表姐已结了婚,生了孩子,但处境很艰难,一年辛辛苦苦连一家子必需的口粮都拿不回,还倒欠生产队的债。我正为表姐的处境担忧的时候(那是一九七八年三月的一天),表姐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说不清当时是高兴还是难过。多年不见,已经三十一岁的表姐,却像个四十开外的女人,她穿着洗得寡白的蓝布褂子,似乎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我的面前。好久,才怯生生地说:“帮我找点事做,看细伢子做杂事都行,一月工资十五块,管饭……”我心里一阵难受,至亲的表姐妹,久别重逢,她却连一声妹妹都不肯叫;而且从她的话音里感觉出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陌生之感。我强抑着自己内心的痛楚,强颜欢笑地说:“咱们几年不见啦,先痛痛快快耍几天再说。”表姐自言自语,又像求我似的说:“我耍不起,要交生产队的粮食……钱……”我见表姐为难的样子,心里一动,脱口而出:“你哪也别去,给我看小华。正因为没人看,小华还托在别人家呢!”
“唔”,表姐涨红了脸,“愿意是愿意,不过……又要增加你的开销。”
我拍着表姐的肩膀说:“小华她爸是地质队的,有野外作业补助,半年才回来一次。每月给表姐夫寄二十块回去交生产队,余下的我们花,钱多吃甜,钱少吃盐,没钱喝开水。”表姐感激地点点头。我敏感地觉察出,她瞪大的眼神里,射出一道意外的光亮,那光亮像夏夜的闪电,骤然而来,又悠然而去,扑朔迷离,令人莫测。为了欢迎表姐,我从皮箱底下,拿出桃形相片夹子压在玻璃板下。表姐看了看说:“收了它吧,摆在这多不相称,过去的事,没啥……”过了几天,照片果然不见了。我问表姐为什么藏起来了,她却带着一丝深藏的痛苦,故意把话题岔开了……
自打表姐来了以后,院子里干净了,水槽里的菜叶、剩饭不见了。邻居们都说,这是我表姐的功劳,我心里美滋滋的。可我还不满足,我多么希望,推倒横在我们心里的那堵墙,像过去那样,高兴时她和我一块儿唱歌、说笑、捉迷藏,难过时和我一块儿抹眼泪。然而,我的愿望落空了。表姐和我带着小华在一个床铺一共睡了三夜,到第四天,她坚持另支了一个不到六十厘米宽的木板床。我说破了嘴皮,她也只是笑笑,开玩笑地说:“和你困不安稳,怕你把我‘蹬’了!”更让我奇怪的是,我每天下班回来,她像小学生复述课文一样,把一天发生过的事情统统告诉我,小华拉过一次大便,三次小便,换四次尿片,喂过三次牛奶;邻居来借过一次东西,等等。天天如此,照说不变,我都听烦了,但我若稍有不遂意的表示,她便惶惶不安,手足无措。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