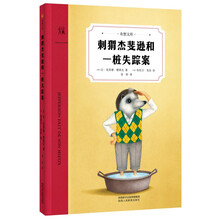妈妈真好
这辈子里,对我好的人太多了,要列名单的话,名单可就会很长很长。可排在第一名的,无论如何一定是我的妈妈。妈妈生我养我不用说,而且对我的体贴入微,真是到死而后已。写我妈妈,我得写一部大书,现在先写其中一小节吧。
我妈妈活到九十八岁。她去世那天的日历,我还压在我的写字台玻璃板下,日期是1993年4月24日。当时,我七十岁。在去世前几个月,她老对我说:“唉,你饭也不会煮,菜也不会烧,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我的确从不进厨房,只好安慰她说:“你放心好了,到那时候,我有钱就上馆子,没钱就下面条,不会饿着的。”
我妈妈很会烧菜,我就习惯吃她烧的菜,不是饭店里那些名菜,而是我们广东的家常菜。只有她知道我爱吃什么,平时我早晨去上班,总会听到她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才想出来今天给你吃什么。”
她爱我爱得的确有点偏心。偶尔全家吃晚饭时,她会悄悄对我说:“晚饭你少吃一点,十点钟下楼来,我给你炖了甲鱼。”我十点钟下楼,她快活地默坐在一旁看我一个人吃甲鱼。她一口也不吃,就喝一点汤。她这样做,是怕我孩子多,我会省给他们吃,自己吃不着。我只好顺她的意。
到她去世前几个月,她不大烧菜了,只是指点保姆买菜烧菜,当然全以我爱吃的为主。碰巧有一次保姆回乡,她只好自己动手。我过意不去,横了心说:“今天我请你当顾问,你坐在旁边,我动手,你怎么说我怎么干。”
可请我妈妈当了两次顾问,我就把她“解聘”了。原来烧菜这么简单,锅热了加油,油热了放菜,加盐去炒就行。我又不笨,这点操作过程一学就会。菜烧得好不好吃,那是要功夫的,是另一回事。
妈妈走后,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福,也下厨了,自己买菜烧菜,尽量回忆妈妈烧给我吃过的菜,迄今已有十年,颇有长进。套句老话说,我妈妈在天之灵知道,可以安心了。
妈妈真好!
怀念阿妈
我有三个妈妈。只有大妈我叫“阿妈”,二妈我叫“二婶”,三妈我叫“三婶”。我的亲生妈妈是“三婶”。我幼年口齿不清,把“三婶”叫成“sumsum”。我特地用英文“sum”这个字,因为发音相同,如果把前一个“sum”读成我们四声的第四声,把后一个“sum”读成第一声,那就是我叫她的声音了。她曾开玩笑对我说:“我把你生下来,你没叫过我‘妈’。”
我的爸爸是广东人,长期在上海做生意。阿妈和二婶都住在家乡,只有我的亲生妈妈和他住在上海。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五岁时他们带我回广州。他们在那里造了房子,让大妈即“阿妈”住在广州,把我留下来让她照顾,他们仍回上海。在离开那天,他们生怕我吵闹,特地请阿妈带我去看电影。我最爱看电影了,记得那天去的是国民电影院。我家在文昌路龙津路,国民电影院在文昌路下九甫路,正是文昌路的两头,离得不太远。等到看完电影回家,爸爸和我的亲生妈妈已经走了,可是我若无其事,早把他们给忘了,因此阿妈说我这个人“大情性”,好照顾。
我的“三婶”走了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阿妈每天晚上陪我睡觉,给我在背上挠痒痒、讲故事。阿妈小时候一直在乡下,没读过书,不知道她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童话故事。如今想来,这些童话故事真像后来读到的贝洛童话、格林童话。她的许多故事主角是“熊人”,我后来才知道所谓“熊人”就是狗熊。广东没有熊,可见这些故事都是外地传过来的。记得有一个故事里小主人公夜里听到“熊人”咯噔咯噔吃东西,问它吃什么,它说在吃花生米,其实是在啃骨头。这些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她还跟我讲了一些我们家的家事。她说她曾到过上海,从上海带来广州的那个留声机是她让我爸爸把抽雪茄的钱省下来买的。她很称赞我的“sumsum”,说她能主内也能主外,帮我爸爸做了很多事。还说我爸爸怕她,被她管住了,管得好。
阿妈爱我,我也爱阿妈。我还觉得她十分好看。这话我对一位婶婶说了,这婶婶觉得奇怪,问我我阿妈什么地方好看,我想了想回答说,阿妈的鼻子好看。这位婶婶笑了,好像是笑我。我们没谈下去,反正我阿妈好看,不错,鼻子就好看。可惜她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我在小学里读书很用功,阿妈一点也不管我,学期结束发给我奖品,她就很高兴。她只要我每星期写一封信给爸爸。我家房子很大,我爸爸的堂叔腿骨折,住在我家养伤,伤好后,就和太太住下来了。他们就是四公和五婆。他们的儿子在上海工作,他们是在家乡享福的。四公爱烧菜,大热天也用毛巾裹着头烧菜,所以我家每顿饭菜都很好。星期六、星期日我放假,四公总在星期六下午带我去观音山、沙面等处游玩,晚上上馆子吃了饭才回家。阿妈要出钱,四公从不肯收。星期日我自由活动,看电影,逛永汉路(今北京路)的书店,因为我乖,阿妈很放心让我出去,给钱让我看电影和买书。不过我总是趁开学时大买一批书。楼下书房放满了碑帖和《芥子园画谱》等等,我在那里学画画和写字,楼上空着的大厅里那书橱塞满了章回小说以及福尔摩斯探案等等,看小说就在那里。
1936年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