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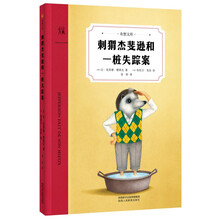
他,那个烟雾中的男人,仿佛从天而降。
起初,他不过是一道影子,是灰暗中的一个黑斑。但随着越来越近,他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变成了一面咚咚作响的鼓。那个人在冲我大喊,但喊叫声从我的耳朵反弹回来,化作了恐怖的回声。他伸出长长的手臂,距我仅有咫尺之遥,以至于我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是汗臭,还夹杂着橡胶燃烧的焦煳味。
他靠了过来……
凌晨三点零五分。
绿莹莹的时钟数字在黑暗中回望着我。街灯的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渗入我的房间。四周万籁俱寂,那个人已经走了。原来是一场噩梦。尽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不只是一场噩梦。
那天早上,我比平时多磨蹭了一会儿,因为麦洛赖在花园里不肯进屋。它发现了一只小田鼠,正像疯了一样东跑西蹿。最后,我终于把它扯进屋里,一边打扫爸爸剩下的早餐,一边等我最好的朋友露露。爸爸上班去了,还在厨房的餐桌上留下一张字条:
晕晕,放学后见。祝你今天开心。
往常露露都是八点四十五分就到的,一分钟都不差,所以我们路上也不会特别赶。可是现在已经快要八点五十分了,她还没有来—肯定是时间紧迫,她决定自己先去学校了。我不能再等了。
一出门我就狂奔起来,双脚拍打在马路上,与我的心跳正好合拍。格列佛大道两侧的房屋从我身边闪过,初秋的冷风灌进我的耳朵,刺得里面隐隐发痛。一大群人正挤在公交车站,像一团灰色的云,掠过我的身旁。路上的车子汇成一道流动的小溪,里面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白和黑—那是写字楼和银行员工的制服颜色。
我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学校门口才停下。我手撑着大门栏杆,胸膛像是要炸裂一般。铃声早已响过了,就连平日里挎着宽松帆布书包、挽着运动服袖子、成群结队的六年级学生也都不见了踪影。我走进空空荡荡的大厅。
露露正站在储物柜旁,不满地瞥了我一眼,对她为什么没去我家只字未提。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她经常抛来这样的眼神,我早已经习以为常。自从上了八年级,露露总是摆出一副万事通的样子,从衣服、发型、音乐,甚至到选择约会的对象。
“你怎么总是赶着点儿来?瞧瞧,你裙子上沾了什么?”她摇了摇头。我没理她。露露的裙子短得离谱,可我从不多嘴。最近为了显摆她那皮包骨般的膝盖,她总是把裙边儿掖起来。她打算以新面貌示人,甚至还拉直了头发,画上浓浓的眼线。
“走啦,伊兹,快点儿!”
还不等我问她为什么没去找我,露露就转过身,消失在去往教室的路上。我站在原地,想着她说不定会随时站住,回过头来等我。可她并没有。
“伊兹,你怎么还在这儿?”麦肯齐先生似乎很生气,“站在走廊里做什么白日梦?已经九点零五分了!快去上课!”
前两节课是数学。克鲁纳先生像往常一样,在教室前面大步地走来走去,一脸茫然的表情,似乎在神游仙境。我很喜欢他,虽然他的课讲得不怎么明白,但为人和气又风趣。
温馨提示:请使用员工书屋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