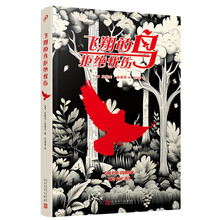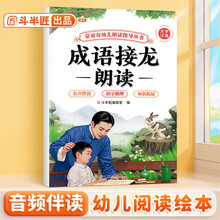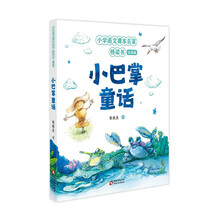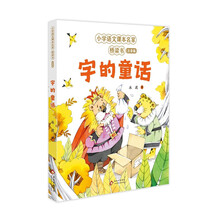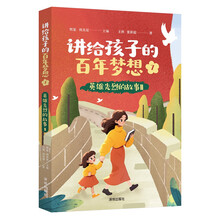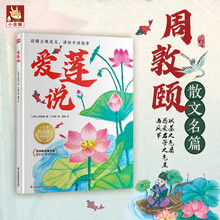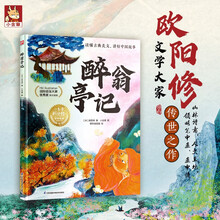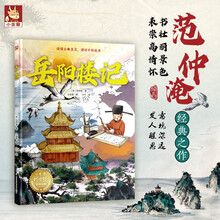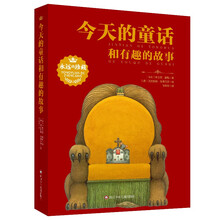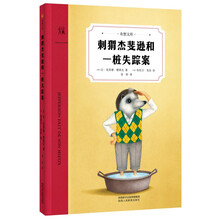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沈石溪和他的朋友们:狼王赴死》:
打洛江边的幽魂,一直令我难以释怀,我碰上什么东西了,是谁捣毁了蚁巢?
暑假中版纳最闷热、最潮湿的日子里,我又径直来到打洛江,一是想探个究竟,二是非要搜寻到酸蚂蚁不可。
说到酸蚂蚁,那可是与版纳人从小契合的无法割舍的可爱的小不点儿。
其实,所谓酸蚂蚁,不过是热带雨林中一种细长的体形较大的黄蚂蚁。但是奇特的是,它的腹部下方有一个透明的储酸小黄球。捉一只酸蚂蚁放在鼻子下嗅,一种独特醇香的酸味令人忍不住想打喷嚏,整个鼻子都酸溜溜的。捉一大捧酸蚂蚁,密封在罐子或瓶子里,过一段时间,酸蚂蚁的酸汁儿慢慢被浸渍出来了。倒出一点汁液,连同酸蚂蚁拌生肉或凉菜,酸中微甜,风味绝了。
版纳人喜酸,制作的酸醋大多来自天然原料,其中“酸蚂蚁醋”是最上乘的。
可更爱酸蚂蚁蛋。
因为酸蚂蚁个体大,它的蛋也较其他蚂蚁大,一粒粒有黄豆粒大呢。更因为酸蚂蚁蛋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及其他营养物质,便成了版纳人家待客及滋补的上品。据爷爷说,我小时体弱多病,他专门为我掏酸蚂蚁蛋滋补。别的人家常将掏来的酸蚂蚁蛋用猪油、辣椒、大蒜、盐巴等配料炒黄后加水,煮上十多分钟,做成传统“酸蚂蚁蛋”菜,而我却非要煎着吃,放一大把在口袋里,当炒豆吃。
爷爷分析,我可能撞上穿山甲了。
寨子里谁没见过穿山甲?
版纳雨林周围的村庄葳蕤馥郁,到处湿漉漉的,这要归功于雨林自身的储水功能。最可爱的是一种含羞草科的“雨树”,这些树的枝条简洁、流畅,羽状的复叶密密麻麻地组成了一把绿色巨伞。奇妙的是,无论是高过二三十米、树冠直径达十五六米的大雨树还是高不过头的小雨树,它们的叶子在夜晚或阴湿天气都会像含羞草一样闭合下垂,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包裹在叶片里的雨水、露水便纷纷落下,如雨飘洒。
自己会下雨的不仅有雨树,所有的雨林植物:榕树、棕榈、青皮树、合欢树、榛树、青冈树、麻栎树、箭毒木……都会“下雨”。它们的叶子、树干和气根,每天都会释放出大量的水分,形成每天雨林清晨必不可少的“浓雾”天气。然而,雨季一来,地面便更潮湿了,踩下去都听见刺刺的水声,没有哪一块地面不潮湿,没有哪一个地方不钻出色泽不一的蘑菇来。那时候,最有趣的是,蹲一朵蘑菇旁,看一群蚂蚁排成长长的队伍,通知伙伴们前来会餐,只要一会儿工夫,一朵碗口大的蘑菇,就成了一团褐色的耸动的大蚂蚁球了。
雨林里的蚂蚁可能是酸蚂蚁,也可能是褐蚂蚁,还可能是黑蚂蚁和白蚂蚁……要是家里的粮食不小心放到潮湿的地方,或者收藏不严实,不需要多大的工夫,蚂蚁们便将它们搬运走了。最可恨的是白蚂蚁,虽然傣家的屋子是干栏式建筑——过去是竹楼如今是木楼——下层摆放不易损坏的杂物,像粮食之类的东西是要放到楼上的。然而,不经意间,白蚂蚁们便将储物柜之类的东西蛀空,里面的东西更是糟蹋得不成样子。这样一来,专门与蚂蚁为敌的穿山甲们便特别受版纳人家的珍爱——无论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都把穿山甲当作护寨的神灵,不让它们轻易受伤害。
我自己就曾经在寨子周围“捡”到过穿山甲。
它们大多躲在屋子周围潮湿的地方,全身披满了厚厚的鳞甲,只要稍微有点儿动静,便蜷曲成一只圆球,把小小的圆锥状的头、尖尖的嘴巴和四肢都藏在坚硬的“盔甲”里去了,一副怎么摔打我自岿然不动的模样。
“不光我们傣家人喜食酸蚂蚁,穿山甲更把它当主粮,一定是那家伙先你一步了。”爷爷这样告诉我,难道我绊了一下滚下江边的“石头”,有可能是穿山甲?
在将黑没黑透的天光中,我进入往江边那段熟悉的路,穿山甲大都在夜里活动,要碰上它们,清晨和傍晚是最佳时机。酸蚂蚁们不会把蚁包挂在竹干间了,地面上不时有隆起的松软的土包——显然那就是蚁包——酸蚂蚁们防潮的新居。我放轻脚步蹑手蹑脚往前走,在一堆蚁包前蹲了下来——那儿有一条褐色的东西在蠕动,是穿山甲!
那只穿山甲,身体和尾巴加起来足有两尺来长,它正隆起身子,将自己的后爪和前爪搭在一处,卖力地工作。它的前爪坚硬如一把铲子,迅速地将脚下的湿土刨松,而它的后爪更像两只斗,把前爪挖松的土刨到身后去,显然,它在向眼前的蚁包发起攻击。很快穿山甲便得手了,它将蚁穴表层的硬壳撬开时要困难一些,然后,它的工作便轻松了,硬壳之下便是蚂蚁庞大松软的地下建筑了。只见它把尖尖的舌头探进了洞中,开始享受蚂蚁盛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