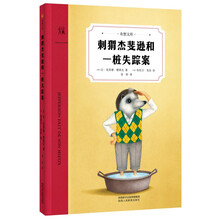他揉着一对红肿的眼睛,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胳肢窝下还夹着昨晚的那本画着九头猫怪的漫画书。他觉察到了我的目光,又打了一个哈欠才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暴恐怖的噩梦。”表弟这几天一个“暴”字不离口,什么暴男、暴爽,连喝一罐可乐也会说“来一暴罐”,“最后,我竟被猫附体了,变成了一只九头猫怪!”
不过,说归说,白天的表弟看上去与晚上判若两人,脸上没有一点恐惧。
他把那本漫画书从胳肢窝下面抽了出来,我以为他要扔到栅栏外面的垃圾桶里去,想不到,他却从我身边绕了过去,打开狗舍的门,把它丢了进去。
姨妈家养过一条名叫“噩梦”的牧羊犬,后来老死了。
三年前我来时,它就已经死了,可表弟一直不让把这个狗舍拆掉。
表弟强迫症又犯了,我看到他明明已经把狗舍的门关上了,还挂了锁头,可他还是把那扇圆形的小门拉了又拉。“别拉了,它又不会变成一只猫冲出来——”若不是我拖长了声音戏谑了他一句,他怕是会跪在那里拉上一百遍。
表弟羞红了脸,这才站了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
他指着狗舍对我说:“这是噩梦集中营。”
“什么……营?”
“噩梦集中营——”一定是一条腿跪麻了,他咧了一下嘴。
我还是不懂。
他跷着发麻的脚,围着狗舍蹦了一圈,嘴里还咝咝地叫着。可能是那条腿恢复了知觉,也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嗓门过大了,他又拍拍狗舍对我说:“这里面装的,全是让我做过噩梦的恐怖漫画书,有几十本了,所以我管它叫‘噩梦集中营’。”
“你的那条狗也叫‘噩梦’!”
我嘴里不知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这不是在揭人家的痛处吗?话一出口,我就恨不得扇自己一记耳光了。我愧疚地瞅着表弟,我以为他会伤心地扭头跑回家去,但他没有。那似乎已经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了,他用一种明快的声音说:“‘噩梦’从来不会让我做噩梦的,它太大了,它只会让那些欺负我的孩子吓得做噩梦!”
他的脸上是一种回忆的表情。
他一双黑色的眸子遥望着我目力所不及的远方,好像是记起了一个童年的朋友。
他真的是长大了。
他那种表情,让我好想怜爱地把他揽到怀里。
后来,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你怕它们,”我瞥了一眼狗舍,表弟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指让他噩梦缠身的恐怖漫画书,“你为什么还要看呢?”
“吓人!”他回答得再简单不过了,“吓人才好看!”
“可你为什么要把它们锁在狗舍里,不丢到垃圾桶里去呢?反正已经看完了。”我坐在秋千上拧起了麻花,“要是我,”我一直等到我不再旋转了,“我会把它们送人。”
表弟沉思了一会儿,看着我说:“我想再过几年,等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再把它们拿出来看一遍,看看我还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做噩梦。”他的目光像一个成熟的男人:“要是我不再害怕了,不再做噩梦了,就说明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坐在秋千上,就那么杲杲地望着在一瞬间挺拔起来的表弟,在心底暗暗地说:表弟,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有好几次,姨妈都又是嫉妒又是羡慕地对我说:“小弟只有和你在一起时,才会一本正经地说些大人的话。和我们,哼……”
他大概是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把目光投向了狗舍:“到时候,我就会亲手把它拆掉。现在嘛,”他又蹲下了,对着他那个远逝的朋友曾经的家说道,“先让‘噩梦’的灵魂替我守着这些漫画吧!”
不过,他很快就又变回一个十岁少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