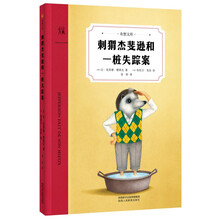生命
毛毛:也许我们那天在铁路上真的错了。
我:什么事错了?你怎么啦?
毛毛:我也说不清。那天,如果我们三个人不说那些话,结果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我:毛毛,你在说梦话吧!请你说清楚一些。
毛毛:我也说不清。
我:那就闭上嘴。
毛毛:真的,那天,如果我们三个人不说那些话,结果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原定我和毛毛、药瓶三人去市里看著名歌星演唱会。我们急不可耐地等了一个星期。结果药瓶在昨天夜里一个人上街闲逛,被人家认出了他是药瓶,四个小子把他堵在不透气的死胡同里,用一把菜刀顶住药瓶的瘦长脖子(那时候,药瓶肯定像个名副其实的盛满人参蜂王浆的药瓶子)。四人轮番打他耳光,一人揍他二十五个耳刮子,凑足一百整,才放了他。那四人在胡同口一消失,早已支撑不住的药瓶顺墙软瘫在地上,感到自己的脸怎么失了知觉。伸手一摸,像触在一头肥猪的屁股上,意识是自己的,脸是别人的了。他手上湿乎乎地发黏,肯定不是什么强身的蜂王浆,是自己委屈透顶的血。我半夜得到消息后,叫了毛毛,前后脚溜进药瓶家。药瓶的父亲和母亲端水喂药,把药瓶侍候成一个末代皇帝。他们回头看见我和毛毛悄声立在门口,脸上就变了色,不说一句话。好像是我背地里勾结那四个浑蛋,暗算了他们的独生子。
药瓶的父亲是县医院的接生大夫。这一点,我和毛毛始终搞不清,连药瓶也不理解,一个男人去接生,总有点不对头,奇怪的是药瓶父亲连年被评为优秀医务工作者。我们三人正经讨论过药瓶父亲的手,那双手接下了一千余名婴儿,没出现一次医疗事故,想必那双神奇的男人的手,让世上多少温柔的女性的纤纤玉手望尘莫及呀。
我站在门口正不知是退出还是挨近受伤的药瓶,药瓶的父亲早已逼近了我,突然揪住我的衣领,一拖便把我拖到门外,他又用后脚跟把门踹严实,回头盯着我,好像我是一枚会随时爆炸的臭弹,会伤害所有人。
我心想,药瓶的父亲太粗暴,我是中学生了,不是一个狗屁不懂的小孩子了,干吗这么待我?再者,这老家伙就这么粗手大脚地去接那些颤颤巍巍的孩子出世吗?他刚才揪住我的瞬间,我觉得我是被机器人劫持了。
我强颜欢笑:“叔叔,药瓶挨打,我一点都不知道。如果知道他昨夜会挨揍,我不会离开他的,我会冲上去的!”
药瓶父亲说:“你住嘴,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上我家来,也不要再找我儿子了。你不想考高中,我儿子想。对了,请你以后不要叫我儿子绰号,他叫赖雅清。”
我说:“赖叔……”
药瓶父亲说:“你赶快离开这里,还有,领上你的毛毛一齐走!”
我的心情骤然一落千丈。
我和毛毛站在北方四月的冷空气中瑟瑟发抖。毛毛问,还去市里看演出吗?我说,挨了一顿训,我们就不会活着了?走。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