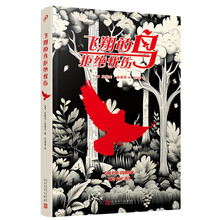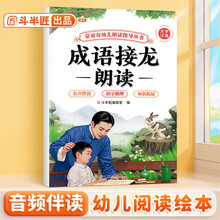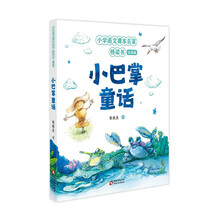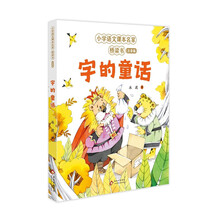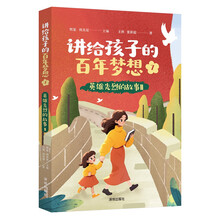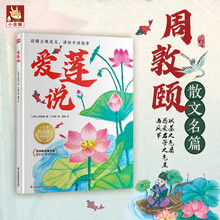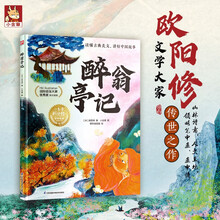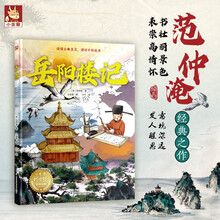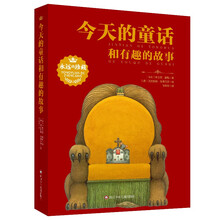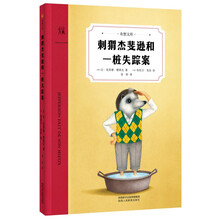二
部队一进大陈村便感到情况异常,老百姓正纷纷扰扰,准备扫荡。他们诧异地问,半夜开走的队伍怎么又回来了?原来有一个团已在这村住过七天,惹得周围据点调动频繁,大有群集扑来的迹象。然而,我们的常营长对家乡过于信赖,事先不曾派个侦察员来了解一下,至今对这一情况还毫无所知。结果,意外很快便发生了。
首先是西北十里响起了枪声。听着这沉闷的穿雾而来的警号,常大胜以为不过是铁路上下来的追兵。现在战士们饥肠辘辘,十分疲乏,而敌人还在十里之外,打个尖还是可以吧。便通知各连,赶紧做饭。这时,教导员郭一旗来了。他认为,大雾迷了视界,情况需要弄清,建议派个班沿拒马河往上搜索一下。营长眨眨眼皮,冷光两闪,却没有吱声。
随即,东边七里又传来“歪把子”的连射,说明下游的敌人正与上游呼应。从枪声判断,又绝不是虚张声势的伪军作怪。然而,久惯战阵的营长依然沉着冷静,他眼睛一转,倒向教导员作了这样的发问:“你看,是不是往东也派个班去呢?”
郭一旗知道话中含刺,也不吱声了。三天前,二连指导员发疟子离队,为谁接他的职位问题,两个人曾有争执,因各执一端,互不退让,于是把这场不愉快一直带到平原上来。其实,常大胜早就认为,这个政治机关派下来的白面书生,当的是教导员,却总以政委自居。这个营自抗战开始,是由姓常的带出来的;军政两把手各司其职,什么“派一个班出去”,难道军事指挥权也想插进来吗?
第三起枪声又从北面冲风冒雪地传来了。常大胜终于明白,大陈村面临着三面包围的形势。
“去,通知各连,”营长向通讯员发出命令,可他又忽眼珠一扫,回到教导员身上,“怎么样,走吧?”
“往哪儿走?”
“过河。”
郭一旗眯起近视眼朝南望去。是的,那边还没有枪声。雪地上一线长堤,由西北斜向东南,远近迷迷茫茫一片混沌,全是雪雾世界。他心里知道:过河五六里,有一条汽车路,是保定高碑店通雄县的要冲,天晓得那儿有没有伏兵呢!
冥冥中的命运之神错着牙齿盯了这一对领导冷笑,看他们怎样在一步步往下走。是的,郭一旗是个宽和人物,多年组织工作的经验,使他太看重人事关系了。他知道营长在赌气,可他的理性不让他对那咄咄逼人的姿态做恶意的理解。大敌当前,还闹什么别扭!于是,他取了忍让缓和的态度,派支小部队去河南侦察一下的建议已到嘴边,却被另一句话顶替了。
“是不是听听丁同志的意见?”
一夜的爬山过路,使地委副书记丁法威还没有喘过气来。三面的枪声他都听到了,但脚底发麻,腿重千斤,又自认军事上是个外行,虽然晓得此去东北三十里,便是根据地的腹心,可他还是附和了营长的意见。敌人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扫荡”,总是从北往南推的。何况营长说了,过河之后,便将小桥拆掉。那么,尽快有个地方舒舒麻木的两腿,是个吸引人的前景啊。 没有人再问一下:响枪的地方必有强敌,而沉静的地方必定保险吗?
部队向南出发了。奉命殿后的三连,带好了锛凿斧锯,等到全体人员过得河去,那道窄窄的木桥顷刻间就被拆掉了。桥下是玻璃似的薄冰,冰下是滚滚的流水,雪片在空中飘摇,郭一旗混搅着满腹的烦扰……
P7-10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