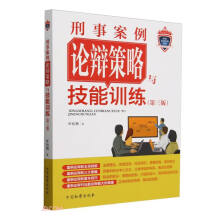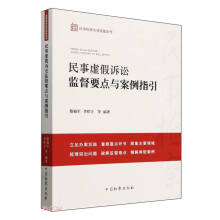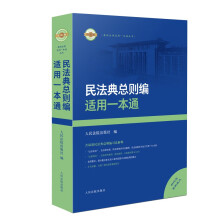《人民法院案例选2021年第10辑(总第164辑)》:
一、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的认定
《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开宗明义强调,共同签字或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所谓共债共签,即便仅在《合同法》框架内考量也应为共同债务,这点并无争议。需要讨论的是本案李某乙所欠银行债务系夫妻一方为债务人,另一方为连带责任担保人,该债务能否视为前述条款规定中的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一种观点认为,类似本案这种债务的形成形式,夫妻双方各自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即一方为债务人,另一方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即夫妻双方的明确意思表示并非一致成为债务人,故该笔债务当然不能使用《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第一条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另一种观点认为,该笔债务中,夫妻一方为债务人,另一方为连带责任担保人,但夫妻双方对于债务的形成及负担是明知且同意的,因此,对于债务的形成及负担构成共同意思表示,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也即缔结婚姻后,夫妻各自仍然保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的意志。夫妻作为平等的主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有权知悉涉及婚姻家庭利益以及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的重要信息。在此前提下,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共同债务行使平等处理权,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双方地位平等、享有平等处理权的应有之义。《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所强调的是“夫妻一方在形成夫妻共同债务时,应当尊重另一方的知情权、同意权、决定权”。本案中,在李某乙和王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乙作为借款人,王某向银行出具书面承诺并以其单独所有的房产为上述债务提供了抵押担保。如此,王某对于李某乙借款一事应为知情且同意。李某乙作为借款人负担借款,该行为显然并未侵犯妻子王某的知情权、同意权以及决定权;相反,王某作为该笔债务的连带担保人,更能说明其夫妻二人对于借款的发生及负担已然有了充分的考虑,享有了平等处理权,其二人对债务的形成及负担有着共同的意思表示,故李某乙所欠银行借款理应视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至于王某辩称李某乙改变了借款用途,银行贷款实际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笔者认为,《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中提及的借款是否用于夫妻日常生活或是共同生活经营的认定,应从债权人的视角加以评判,即以借款合同签订时债权人明知或应知的意思表示内容为准,作此理解,理由有二:一是债权人在将款项借出后,一般即丧失了其对款项的控制权,在借款后再行要求债权人监督款项的实际流向,实践中难以操作;二是借款用途系借款合同内容之一,借款人在借款后擅自变更借款用途,却让债权人承担其擅自变更用途而导致的不利法律后果,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则相悖。因此,判断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借款时约定的借款用途为依据,而非以借款后的实际款项流向为标准,即便李某乙事后改变款项用途,该银行借款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父母代子女偿还债务,该出资行为性质认定
父母给予成年子女经济帮助,在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且多数并未明确是借款还是赠与。对于父母出资为子女偿还债务的行为性质如何认定,法律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也只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置房屋行为认定。依据上述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双方为子女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前提是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置房屋的行为,首先应尊重父母子女间对出资行为性质的约定,只有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才可能涉及上述出资行为性质认定为赠与的问题,显然婚姻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并不适用本案。对于本案中原告的出资行为,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出资行为系赠与,无论子女是否成年,当子女遇到经济方面的困难,父母为了减轻子女负担对子女进行资助,这是父母对子女应尽义务的延伸,从常理上说属于赠与关系,不需要归还;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出资行为系借款行为,即父母在子女经济困难时,除书面明确表示赠与外,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父母对子女的出资,除书面明确表示赠与外,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