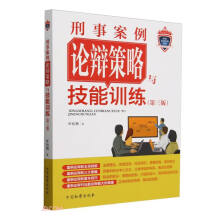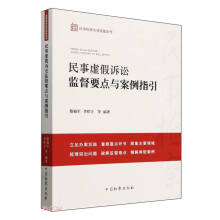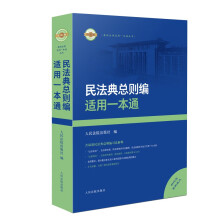《人民法院案例选2021年第11辑(总第165辑)》:
二、规范梳理:不变的概念内涵与限缩的保护边界
(一)不变的概念: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驯养繁殖物种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否包括驯养繁殖动物,动物学界有不同观点,主要有强调生长状态的野生性、天然性的生长状态说,及“凡生存于天然自由状态下,或者来源于天然自由状态的虽然已经短期驯养但还没有产生进化变异的各种动物”的生物学属性说。从法学的角度,2000年《解释》第一条是将驯养繁殖动物纳入野生动物的刑法依据,这一规定招致了系超越刑法文本进行的扩大甚至类推解释的诟病。但是,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中增设了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明确犯罪对象为“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显然从逻辑上认可野生动物包括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和人工驯养繁殖两种类型,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野生动物分为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一致,表明了明确而连贯的立法态度。
(二)流变的精神: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边界限缩
由于将驯养繁殖动物一概纳入刑法保护,在一些案件中造成了罪刑失衡的结果,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出台司法政策进行纠偏。如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指出:由于驯养繁殖技术的成熟,对有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商业利用在某些地区已成规模,有关野生动物的数量极大增加,收购、运输、出售这些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实际已无社会危害性,建议修订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实际已不再处于濒危状态的动物从名录中调整出去;或者修订司法解释明确,对某些经人工驯养繁殖、数量已大大增多的野生动物,附表所列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仅适用于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不包括驯养繁殖的。2020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第九条规定收购、出售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是否构成犯罪,应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及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至2021年2月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公布了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明确梅花鹿等61种野生动物仅限野外种群被列入名录,其人工种群不再属于刑法的保护对象。
综上,我国规范体系采取了“原则+例外”的模式: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的物种,原则上属于刑法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梅花鹿等61种野生动物的人工种群,不再属于该罪犯罪对象。但是,从文义上终结了野生动物与驯养繁殖动物的概念争议,不意味着彻底解决了驯养繁殖动物的刑法保护限度问题。存在争议的问题还有:第一,除梅花鹿等61种野生动物外,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保护的其他456种野生动物的人工驯养繁殖群体,刑法如何进行保护?如“深圳鹦鹉案”中,涉案鹦鹉大多数属于人工变异种,人工种群就包括了人工变异种,是否所有人工变异后的种群都属于犯罪对象?第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只列明在我国境内自然分布或有自然分布记录且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不包括原产于境外的野生动物,非法收购、出售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Ⅱ的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物种行为,其司法认定仍不明确。本案中的费希氏情侣鹦鹉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动物,非法收购、出售驯养繁殖的费希氏情侣鹦鹉行为如何定性处罚?第三,不具有刑事非难性的涉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群体的案件,应采取何种刑法路径实现罪责刑相统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