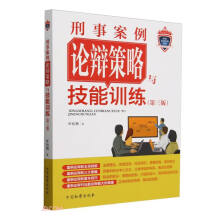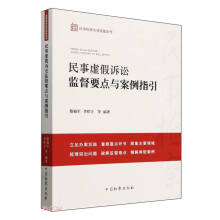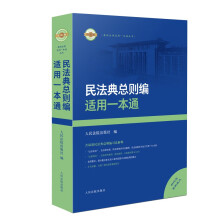(一)裁判文书论证的发生
事实上,法官审理案件,随着案件的逐步展开,有关的所有证据、事实、行为以及法律规范都罗列在大脑中,案件怎样判决,或者说该案件是什么结果,在大脑中随之逐步形成。法官大脑中形成判决——逻辑学称之为判断、命题——本书区别为论题,如何以形成判决的依据证明其判决也随之形成,并思考如何将零散的证据连接成片,与结论联系起来。这个过程,是法官在内心中向自己论证其结论。
如此,法官裁判案件,如果需要论证,那说明法官对案件中需要论证的问题已经有了论题——结论,然后为自己的结论寻找理由。这个论证的过程就是法官“寻理”的过程。如此,是否意味着法官违法了法律规范——事实——判决的顺序,未审先判,先人为主呢?其实不然,因为法官“内心之判”,我们可以称之为“预判”,是在其接触案件后通过与当事人的庭前会议、开庭审理的办案过程中,对案情的由表及里、由浅人深的了解、把握后逐渐形成的。
因此,在法官看来,论证是法官说服自己,而说理则是说服别人。这是论证与说理的基本区别。例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说:“张某主张20年的残疾赔偿金无法律依据,应按其定残时年龄计算17年。”
“张某主张20年的残疾赔偿金无法律依据”,这是法官不支持当事人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即反对“张某主张20年的残疾赔偿金”,需要的是说理——就当事人而言是主张因而需要论证。与之不同,“应按其定残时年龄计算17年”,这是法官的主张,需要论证该主张是如何成立的。
(二)裁判文书论证的性质
法官内心论证完毕,兼以法律适用,诉诸以文字,成为裁判文书。此时,法官由向自己的内心论证转化为外在的对外论证——对当事人、二审法官、社会公众。
因此,所谓裁判文书的论证,其实是法官对自己的“预判”,找到依据——逻辑上的论据,以一定的论证方式将论据与论题连接起来,通过文书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一种智力劳动。
既然逻辑是人类思维的规律,人要思维便离不开逻辑。法官是人,裁判案件必需思维,裁判便离不开逻辑。裁判文书是裁判的文字表现,裁判文书便离不开逻辑。既然论证是通过论据证明论题的逻辑方式,裁判就是证明裁判结果的论证,裁判文书的生命就存在于论证之中。何况,现行诉讼法都认为对其裁判予以论证是法官的义务。
如前文所述,形式逻辑囿于其“形式”上的要求,其论证不能适用于裁判文书论证。如果说这个结论稍嫌笼统的话,需要将形式逻辑的前期——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数理逻辑区别开来讨论。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逻辑,如前所述,并没有严格形式化,而是已经孕育了辩证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因而,在特别情况下,传统逻辑的论证不排除适用于裁判文书的可能性。
可是,当传统逻辑演化成数学演算,发展为数理逻辑时,尽管其科学性已经为计算机语言的成功所证明,但数理逻辑的论证无法适用于裁判文书,只要受过法律训练,即可认识到这一点。
虽然如此,但这与裁判文书应该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并不矛盾。
由于裁判基于控辩或诉辩双方的论辩,任何一方的论辩都不会采用,实际上也不可能采用科学上的证明性论证,只能采用日常生活中的论辩性论证。法官在此基础上论证自己的论题时,也只能采用论辩性论证,最终将表现在裁判文书中。而亚里士多德之论辩性论证,发展变化至今天,裁判文书论证实质上是非形式逻辑论证。
如果法官把握了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异同,在裁判文书中裁判娴熟地运用逻辑论证,裁判文书的生命力将跃然纸上。
三、裁判文书论证的特征
裁判文书论证之所以性质上是非形式逻辑的,因为只有这种逻辑论证才具有合情性、可接受性、可废止性三个根本特性。而且,这三个特性决定了裁判文书也同时具有这三个属性。反之,如果裁判文书缺少了合情性、可接受性和可废止性,则不能成立。
(一)合情性
合情性是指适合人的情感,人之常情,亦即情理。情感是人的人性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合情性宽泛一点,也就是符合人性。
裁判文书论证是对裁判结果的证明,以说明为什么是此种结果,也明确了不是彼种结果。
裁判文书是保障法律实施的书面形式,法律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裁判文书论证如果不合情,不仅不能为当事人所接受,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不能实现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之目的。
(二)可接受性
裁判文书论证的可接受性是指论证的形式、过程、结果,可以为人们所接受。载于裁判文书中的法院裁判,固定或变更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直接影响了当事人的生活。更广泛的意义是,裁判还影响甚至决定了人对已有的同样行为的反省和未来行为的取向。如果裁判不为人们所接受,预期的效果不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可接受性也指向某份裁判文书中的当事人,但实际上是包括该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因此,当事人接受的论证并不一定具有可接受性;反之,当事人不接受的论证,未必不具有可接受性。
当然,裁判文书论证的可接受性,在不同的地域未必相同,尤其接受的程度会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个地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不同的历史阶段,可接受性的差异更大。甚或说,在前一个时期具有可接受性,而后一个时期则不可接受。
究其原因,一方面,裁判文书论证的可接受性本质上源于合情性,而情感之于人,在不同的地域有所差异,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更甚;另一方面,不同地域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论证所使用的论据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