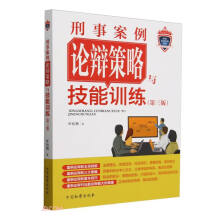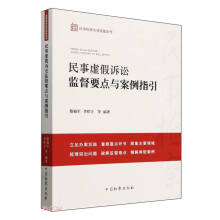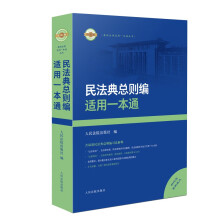本案例的争议焦点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投资者钱款的目的,至案发,艺术品投资公司收取的佣金大部分均没有动用,也没有挥霍、隐匿等情形。行为人虽利用免佣金账户自买自卖进行对倒交易,但这系一种赚取差价的投机行为。至于资产包内艺术品的价值,随个人喜好不同而相差极大,不能以衡量一般商品价值的方法进行估价;通过案发后相关部门组织的重新估价,由于带有不同评估人员的主观判断色彩而缺乏客观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行为人采用虚假宣传、虚构艺术品资产包真实价值、隐瞒免佣金账户的存在,自买自卖进行对倒交易、控制艺术品资产包的份额价格与交易总量,造成虚假繁荣的假象诱骗投资者投资,从而骗取了投资款。艺术品的价格虽与一般商品有所不同,但不能背离市场的一般规律,艺术品鉴定人员在没有实地验货的情况下直接出具评估报告,将价值仅2900余万元的资产包虚假评估为58亿余元,明显具有欺骗性,应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行为人采用欺骗手段,以艺术品资产份额化交易为名设立资金池,吸收3.6万余名投资者累计投入资金达110余亿元,并造成1万余名投资者损失达40余亿元,无论是吸收的资金总额还是造成的损失均特别巨大,应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传统的集资诈骗案件审理过程中,刑民如何界分始终是金融犯罪案件审理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司法裁判者通常从非法性、社会性、公开性和利诱性四个要件予以回应,对案件事实抽丝剥茧以便与法律规范“对号入座”。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行为模式的变化,民间借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更具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统一性,尤其在非法集资的对象因互联网技术呈现海量扩张的样态下,个案的特殊性与法律规定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本案作为一种新型犯罪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艺术品资产份额化交易主体鱼龙混杂
从艺术品资产份额化交易的背景流变中可以看出,多地推出了此种新型交易模式,并出现了“文化产权交易所”“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等不同称谓。根据我国的规定,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文交所)是指依法设立,集文化版权、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类文化产权权益为交易对象的专业化、市场化平台。而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则主要从事文化艺术品交易服务、文化艺术品投融资服务,主要操作模式是将文化艺术品以期货方式在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因存在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国务院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以下简称《整顿交易场所决定》)对此紧急叫停,对份额化交易、集中竞价、持续交易等交易模式有严格限制,必须依法设立或经国务院、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对交易的对象也要求不得超过200人,交易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以此方式来控制风险。但《整顿交易场所决定》颁布以后为应对禁止性规定,实践中出现了为规避凡使用“交易所”字样需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规定,行为人以金融创新、金融改革的名义在香港等地设立交易平台,在自贸区设立代理公司,以自贸区负面清单对此没有禁止即可以开展艺术品资产份额化交易为由,意图规避我国对艺术品资产份额化交易的审批,意欲以舶来品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进一步混淆了交易主体,使投资者难以辨别。
(二)高度抽象的秩序法益难以证明
金融活动充满了复杂性,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泾渭分明,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作为法规制对象的复杂性急速增加,当初立法时未曾出现也未曾想到的问题接踵而至,不仅给司法实务界带来了挑战,也给理论界带来了研究困难,新型金融行为是否触犯了法益或者触犯了何种法益,因其高度抽象性而成了难以证明但也难以反驳的一个现象。1995年,我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将金融秩序作为基本法益,金融管理秩序与金融交易秩序为法益子系统,①秩序法益观由此生成,它奉行以国家金融秩序维护为法益选取根据的基本立场,是国家本位主义刑法观的具体化。1997年我国《刑法》对金融犯罪进行了类型化的设置,分设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两节,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涉及的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集资诈骗罪因增加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构成要件而被放在金融诈骗罪一节。②上述法律规定无不凸显了秩序法益观的立法倾向,并在司法裁判者的心中根深蒂固。在秩序法益观指导下,违反金融管理秩序即可以成为人罪的依据,金融犯罪庞大的资金体量导致一旦违反金融管理秩序,常常会跨越行政处罚直接进入刑事处罚,刑法被看作维护金融秩序的常用手段,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成为此类案件法庭上辩论的重点。但由于秩序法益的高度抽象性,裁判者无法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破坏了金融秩序作出有力的回应,辩方也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辩护主张推翻公诉机关的指控,导致“金融秩序的破坏”这一构罪要件成为法庭上听得到但看不到的“风景线”。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