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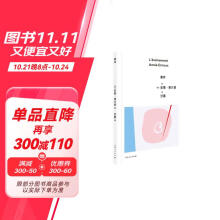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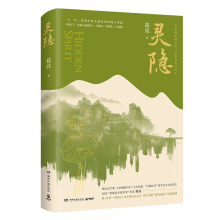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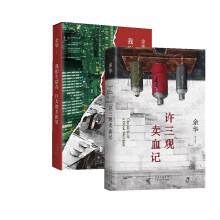








梅朵,从内地来到西部高原藏区支教、帮扶,在那片雪山环绕的原始草原,她与孩子、牧民、扶贫干部们,艰难而温暖地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面对困境,她的爱和帮扶,从哪里开始?
孩子们紧锁的心扉,她怎样用心去叩开?
脱贫攻坚的草原人,怎样用汗水浇灌未来?
草原孤儿学校的孩子们,长大后过得怎么样?
远方的月光,身边的班哲,谁是她的情感归宿?
当春风吹进草原,身患重病的她,何去何从?
当你读完梅朵与草原的故事,或许会有那么一瞬,在月光下,在感动中,你的泪光,已晶莹成一朵盛开的雪莲花。
你将刻骨铭心地领悟: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帮扶?
正如作者江觉迟所说——
“爱,就是把你变成被爱的人中的一个,有他们的气息,和他们过一样的生活,如此才能融入他们,并让他们接纳你的爱。”
《雪莲花》,把爱与坚韧,留存于雪山和草原。它不仅仅是《酥油》的续篇,它告诉你,《酥油》里描绘的那片深山草原,如今,变了的,和没变的。
1.月光
时常,我想起一句话:漫游的人对于远方、对于理想,比他对自己的身体、脚步更为信任。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信念,才让我走过了很远的路,结识了很多的人,同时也经受了太多复杂的事。
当那些复杂之事难到以我的心智大致也无法解决的时候,我就会去寻求草原上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请求他们的答案。当然,大多会得到老人们这样的答复:你会知道怎么做的!那口气的肯定,也像一个漫游的人对于远方的肯定——只要心有感应,就不会远。是的,无论怎样困难,能够得到草原人的支持,对于未来的帮扶工作也就增添了更多信心。在过去,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如今想起帮扶中那些事,不论是遥远的还是近期的,总会历历在目。痛苦的回忆经常会有意地避开;得意和温暖的事儿,会像烧酥油茶那样,要不断地添火、加热,没完没了地享用。比如孩子们。阿嘎、苏拉、米拉、达杰、格桑、多吉、那姆、小尺呷和他的阿弟五娃子……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些温暖的回忆,如同月光,逢上失眠的夜晚,总会悄然地映现在心上。
回想起来,孩子当中,最为冒失的要数格桑。我寻到时,他已经十四岁。有点早熟,说话非常大胆。各种能说或不能说的玩笑,他都要说出来。每次见有年轻的男子来我们学校办事,他准会凑上前,不论人家什么情况,总要说:“你和我们梅朵老师耍朋友(谈朋友)吧。”惹得办事的人很尴尬。我也挺生他气的,批评他。一批评,他便满脸委屈,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后来有位女同学悄悄向我汇报,说这孩子常在私下与她合计:我俩给梅朵老师找个阿哥嘛,这样她就不会离开了,生几个娃娃,和我们在一起。当时我听了,心往下一沉。因为身体越发不好,有天我在碉房外狠命地咳嗽,被这孩子看到,问怎么了,我说心口痛,哪天我要回家去。不想这孩子从此记在心上,他是想用这样的方式留住我呢。
有个孩子,平时最喜爱表现自己,且方式有些特别。经常会故意把生字读错,或明知故问地向我提出一些问题,引起我多多关注他。时间长了,他出错时我就会朝他头上轻轻敲一下,说你真笨!他却特别享受这种被“惩罚”的过程。每次出错之前,总会把头早早地伸过来,我们对此心照不宣。
小尺呷是孩子当中最难管教的,特别调皮。上课时经常会故意离开座位扰乱同学,怎么说服他也不听。所有办法都用尽了,实在迫不得已,我只好又去寻求老人们出主意。老人们给我的答复依然是:“你会知道怎么做的。”我垂头丧气地返回学校,心想这些老人是把我的心智估计得太高了,其实我对小尺呷根本没辙!一日,受麦麦乡政府的邀请,我去参加草原上一年一度的耍坝子(草原上的一种群众性的节日)活动。当时气氛相当热烈,有震撼的音乐,嘹亮的歌声,热情的锅庄舞蹈。我无比享受地欣赏一番,回来后就有了主意——调教小尺呷的主意。这孩子天性好动,尤其热爱歌舞,平日一听到音乐,两只小脚就跟筛米似的抖个不停。
周末之夜,我调好学校的音响,把平时的课间操音乐换成热烈的锅庄曲调。我站在操场的礼台上领舞,劲头十足。孩子们则在台下跟着跳起“大锅庄”。一时间,强劲的音乐把校园变成了狂热的舞场。我们都在随着音乐尽情摇摆。但有一个孩子——小尺呷,我罚他站在礼台上方,面对台下所有狂欢的孩子,不准他跳舞。这孩子鬼聪明是多多有了,知道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惩罚他,便佯装不在意,同我僵持。
我们继续狂欢,音乐声震耳欲聋,孩子们在热烈的乐曲带动下完全释放了天性,一边高歌一边狂舞,场景越发奔放。我边跳边窥视小尺呷,见他脸色刚才还佯装不在意,慢慢地却有些把持不住,两腿开始轻轻地点动。我警告他说:“不许动!”他立马仰头望天,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我心下窃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继而调换一段更为强劲的曲调。这时,我开始一边跳舞,一边用高亢的嗓音唱起当地的草原劲歌。所有孩子立马跟着齐声欢呼。我再用眼角余光瞟一下小尺呷,见他脸色已经涨得通红,两腿虽然想竭力控制不动,但那体内好动的天性已经由不得他来控制。他终是憋不住,朝我投来请求的目光。我凑近他,问:“你想跳舞吗?”他先是竭力地抑制情绪,但实在抑制不住嘛,最终只好说:“老师,我错了!”
后来上课时,只要小尺呷一捣乱,我总会附在他的耳边低声问一句:“你不想跳舞了吗?”这办法果然有效,慢慢地小尺呷倒变得乖巧了很多。
那时,咳嗽越发严重,贫血厉害,身上的肉不能碰,一碰到处痛。有天,我在上课,发现有三个孩子不见了。到处寻找,却找不到。后来到很晚的时候,至少九点钟,三个孩子灰头灰面地赶回来。身体虚弱外加过度担心,叫我没有气力责备他们,只能自顾坐在教室的门槛上。孩子们站在门槛外,每人手里拎一包东西。我问他们:“你们跑哪里去了,这拎回的是什么?”语气非常不好。仨孩子一个在微微笑着,另两个则显得有些委屈。不久,就是我自己特别难过了,脸面伏在门框上泪流不止。不知用了怎样的语气,我在责备他们:“你们跑那么远进山,要是遇上老熊怎么办?要是迷路了怎么办?好,就算这些东西能把老师的病治好,那要是你们都没了,老师吃好了还能做什么?”
原来,孩子们是听大人说,有一种藤条的根茎可以治好我的贫血,他们因此进山寻找。其实他们并不认识这种根茎,最终挖错了……
再难叙述!这样的回忆让人温暖又无限惆怅。已经过去多年,如今他们分散的分散,长大的长大。而我,再次回到麦麦草原,再次遥望远方那高耸的白玛雪山时,感觉似乎丢失了它。
25.错觉
经常,桑伽小学的夜晚会变成这样: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校园里,每个黄昏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秋贞老师,他顺着木梯爬上学校土夯平房的顶端去——那是我们一年级教室的房顶。他坐在上面,面对东方的雪山默默地长望。有时仅仅是长望,一直不说话;有时则会对着雪山突发地大吼几声,嗓音粗壮,叫校园里的流浪狗们也要惊得乱叫一阵。再有些时候,他又不望雪山,只会朝着天空昂头,清腔幽幽地唱歌。这时,我们擅长跳舞的孩子们,帮金、次结、其加小孩等,就会不约而同地挤在一起,随着秋贞的歌声摇头晃脑,跳起草原锅庄。慢慢地,歌声会流淌到夜幕里去。如果逢上不好的天气,草原的夜晚,星星和月亮都会躲在云雾里。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蓝得发黑,雪山也看不见。这样的时刻,秋贞仍然会爬上屋顶。但这时他什么也不做,只是望着天空发呆。
我知道,他思念成疾,归心似箭。
孩子们却不知这个。瞧他们的老师立在屋顶上发呆,时间那么长,又不寻望,又不唱歌,就有些等不及。大胆的帮金小孩这时就会悄悄地爬上屋顶去,站在秋贞的身后,故意弄出一点声响。只要秋贞不反对,默许她,她就会代替秋贞亮开歌喉。帮金小孩的嗓音着实好呢,委婉又清脆,犹如风中的银铃。惹得楼下的其加小孩好羡慕,总是忍不住要跟上附和两句。其加小孩一开唱,校园里的流浪狗立马兴奋不已,昂着脖子轰轰烈烈地朝他吼叫。于是,几乎所有孩子都放开了,挤到操场上来,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连最内向的八珠小孩也会尝试地抖动着小脚。
唯独巴巴小孩例外。她从不会跟随小伙伴们唱歌跳舞,也不会因为其加小孩故弄玄虚的嗓音展开笑颜。很多时候我发现,这孩子总是在刻意地躲避着我,回避我的问话。互动嘛,更别提了。
这样的时间过去了一年。
是的,又一年的春天来临了。这天,是周二的上午,四年级的第一节课是语文。我们学习生词。当然,在教生词之前我有个惯例,不会先对生词进行讲解,我要让孩子们凭借自己的想象去理解一个生词的含义。我在黑板上写出“理想”一词,转身面朝课堂,大声询问:“哦呀孩子们,今天让我们学习生词:理想。你们都来说一说,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话音落下,我瞧孩子们,他们却是你望我我望你,答不出话。
确实,如果不是课本上学习到这个生词,我也不想提前谈及它。我平时总是不愿和孩子们谈论理想的话题。因为对于远牧点的孩子们,谈论个人理想实在是有些过早,也有些过分。就像,你都不知道有飞机这个概念,你怎么想象坐上飞机的感受呢?
我听到次结已在嘀咕:“理想啊,我是知道也不知道,有点说不清嘛。”
我就问他:“次结,你的理想是什么?你就把知道的说出来吧。”
次结摸摸头,又答不上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理想,似乎也从未有人跟他提及,所以他只好请求道:“老师,我可以想一下吗,明天再告诉您?”
我朝他笑起来:“理想是会脱口而出的。等你考虑那么久,说出的就不是理想了,是思想。”
我正准备询问下一位,次结紧忙道:“老师,我的理想是变成一只大岩鹰!”
全班哄笑。
管不住手脚的其加立马展开双臂,学着岩鹰飞翔的模样,在座位上摆弄开来,一边口中发出岩鹰扑翅的声响:“呼!啦啦——呼!啦啦——”
全班持续哄笑。
其加见势越发得意,生怕后排的娃娃们看不到,勇于表现,竟然爬上了课桌,“呼!啦啦——呼!啦啦——”他在兴奋地持续地叫喊,“呼!啦啦——呼!啦啦——呼!啦啦——”
他怎么就停不下呢!而我的目光已经随着这个孩子晃荡的身影模糊起来——这是多么熟悉的姿态……是的,我已经看到自己的手,它游动在黑板上,在抄写生字。小尺呷呢,抽身爬上课桌,闪身快速跳出窗口,又闪身快速跳回来。他像一只猴子迅速完成所有动作。课堂上孩子们哄堂大笑。我却不明白,回头看,孩子们个个都是安稳地坐在位子上。我转身面对黑板继续抄写。小尺呷等我一转身,故伎重演,再一次跳窗。这次没准备好,返回时只听他咚的一声,掉在课桌下,摔得四仰八叉。
“小尺呷!”我终于朝他厉声大喊,“你给我站出来!”小尺呷不服,不动身。我一步跨下讲台,一把揪住小尺呷,把他提上讲台来……
这时我听到其加在大声喊冤:“老师!老师!我不是小尺呷!”而全班孩子均被我的喊声骇住了。他们愣在那里,惊讶地望着我。我只得慌慌放开手,匆忙别过头去,竭力地克制。好一阵后,才把恍惚的思绪从回忆中拽出来。
课堂上,其加已经返回自己的座位,但仍然朝我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不知所措。所有孩子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而我已经恢复了常态。我在咚咚地敲黑板,大声说:“安静!安静孩子们!”一边追问次结,“你为什么想变成一只岩鹰?”
次结这回不假思索:“因为岩鹰可以飞翔,比脚步跑得更快。”
南山沟的多吉听次结这一说,急忙跟着发言:“老师,我的理想是变成一只雪豹,一只强壮的雪豹!”
其加此时也立马明白过来,抢着答话:“老师,我的理想也是变成一只雪豹!一只强壮强壮的大公豹!”
这回所有小孩总算明白了什么叫理想,于是各抒己见。有小孩说想变成一头牦牛,因为可以挤奶,做黄亮亮的酥油;有小孩说希望变成一匹大马,因为可以骑着它去拉萨;帮金则说自己想变成一只画眉,因为可以唱出动听的歌儿。其加一听帮金的理想,神情立马又后悔了,呼的一下朝我举起双手。
“其加,你又想捣乱吗?举双手,你是想回答问题呢,还是举手投降?”我故意问。
其加急得不行,说:“老师,我不是投降,是回答问题!”
“那发言要怎样举手?”我问。
其加就把左手缩下去了,大声解释:“老师,刚才我说错了,我的理想是变成一只强壮强壮的大画眉!”
全班一阵哄笑。
却听次结在反对他的阿妹:“不行!你不能变成画眉!我们是一个阿妈的娃娃。我是大鹰,你怎么是画眉?”
全班再一次哄笑。小孩们乐得不行,捧腹大笑,四仰八叉。
这时我发现有个孩子,巴巴小孩,面对这么欢腾的场面,她却无动于衷,垂着头,在玩弄自己的两只小手。我记得第一次见她时,其加说她是苦脸巴巴,难道这真是一个不会笑的孩子?
我走向她,朝她缓缓弯下腰身,轻声问她:“巴巴,你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可以跟老师说吗?”
温馨提示:请使用员工书屋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这是一部让人看了既感动又心疼的小说。美好、纯净的爱情,醇厚、野性的藏区风景与其中的大爱、感动、悲伤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梦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盏酥油灯。江觉迟的那一盏,点燃在遥远的藏区草原。她是幸运的,遵循了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她比很多人活得更体面和奢侈。
——姚晨
我为梅朵选择留在高原而震撼、起敬,更为梅朵最后无奈离开的柔弱而感动、伤怀……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普通的生命。梅朵所以让我不能忘怀,正是因于此:她生命中的强和弱,都被那片神奇的土地成倍地放大了。
——麦家
我真的是被感动了。怎么说呢?也许并不是所谓“感动”能够概括的,准确地说,是一种力量,一种梦想的力量,传递到了我的身上。有些人想做,但下了一辈子决心都没能做到的事,有些人在一闪念中就去做了。江觉迟是后者。人的精神财富大于一切,而江觉迟,内心的富足证实了这样的财富。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潘石屹
为了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一个庇护所,梅朵在草原上坚持多年。无论是对草原孩子的爱,还是对青年月光的爱,都是那么的真诚。她让我们在感动之余,心存温暖。
——安意如
江觉迟在高原上经历的苦难,就像她小说里描述的雪崩一样,让人震撼。那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苦难。所以除了对她作品的欣赏,她个人的精神更令人敬佩!
——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