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国难方殷,贺麟于战时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撰写《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刊于昆明《思想与时代》创刊号。文中首次揭橥“新儒家”旗号,呼唤“建设新儒家思想,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对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复兴的关系做了新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反孔教的激进反传统主义为特征的思想革命,启蒙者信奉革故鼎新的进化论和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主张:“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
贺麟不赞同这种古今断裂的激进文化观。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连续体,现代与传统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儒学的发展,是现代与古代的融合。“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鸦片战争以降,追求泱泱古邦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复兴,是百年中国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伟大目标。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中,哲学家贺麟尤为关切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华文化的复兴,他将儒学的复兴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在贺麟看来,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激烈地反对虽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落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
关于新文化运动之批判传统的思想革命,贺麟予以高度评价,将其视为中国文化古今转型的契机,盛赞其之于儒学开新的重大意义:“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之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
贺麟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为古老的儒学提供了一个去芜存精、推陈出新的现代转型之契机。
对于新文化领袖胡适“打孔家店”之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和提倡诸子之学的“由经返子”主张,贺麟颇表赞同。在他看来,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预备工夫。提倡诸子之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驱。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收诸子的长处,从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就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大放光明。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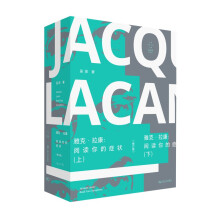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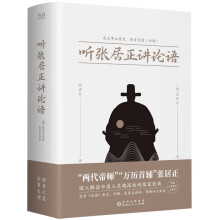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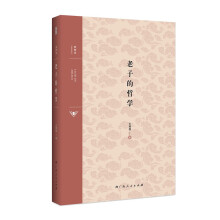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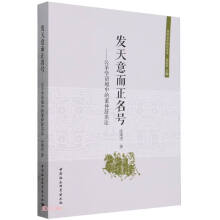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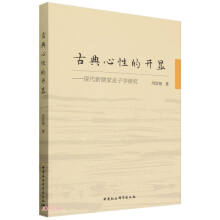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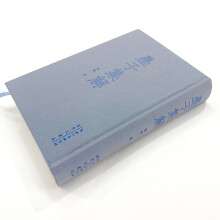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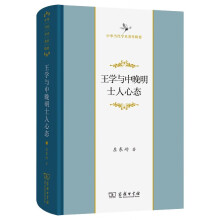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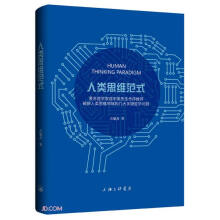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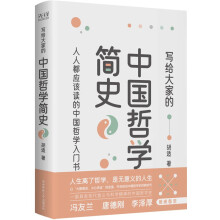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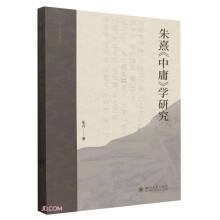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十分拥挤的领域,但高力克教授的着作仍有颇多新意。特别是,高力克教授擅于从国际国内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全面分析晚清以来以“救亡”和“图强”为目的的中国式启蒙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这一知识社会学视角不仅体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反思能力,还表达了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
——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高力克教授治中国现代思想史三十余年之久,对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尤为精深。他的着作关涉古今之变,论及中西遭逢,在纵横交错的视野中,探寻思想人物的精神世界,辨析核心观念的来龙去脉,阐释“新启蒙”思潮的丰富意涵与内在张力。“启蒙三书”中对西方现代性的借鉴与质疑,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反思与转化再生,以及学术、政治与伦理等议题之间的交织互动,呈现出一幅生动而恢宏的思想史画卷。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