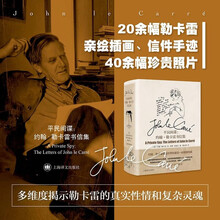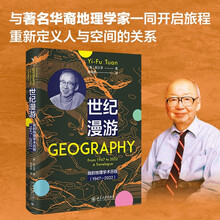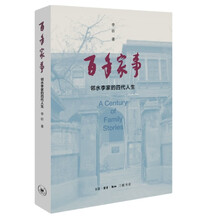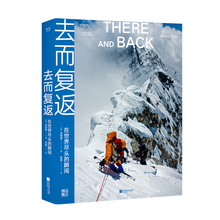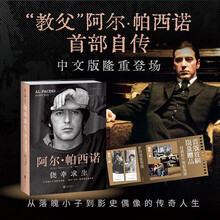我是1896年12月6日在江苏省泰兴县出生的,那时清王朝还统治着中国,用的旧历,是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这一年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清王朝的统治久已摇摇欲坠,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亡国的现象更加迫近了。中俄新约、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德租借胶济条约、中俄租借旅顺大连湾条约、中法租借广州湾条约等陆续签订,至于台湾全省的割给日本,那是甲午战争的直接结果,还不在其内。瓜分中国的形势已经完成了,但是在我的家乡,对于这个情况还不清楚。
泰兴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在长江北岸,扬州东南,两千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所以西汉枚乘《七发》说到“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又说“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西汉初年的长江口正在扬州东南,泰兴还位于江中,近年在城东发现大鲨鱼的骨骼,正是绝好的证明。由于江沙淤积,到第十世纪前半期,泰兴县才正式成立。在我出生的时代,据《光绪泰兴县志》,泰兴人口,只有三十万左右,当然是个小县;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万,就不能算小了。
朱姓在什么时代移居泰兴的?据《朱氏宗谱》说,南宋初年左都御史朱宝明看到当时统治者对外屈服,因此跨马渡江,到了泰兴,下马一看,原来是一匹泥马。后来在朱氏宗祠里为这匹马塑像,祭祠的日子还得为马上祭。这件事怕不一定可信。第一,宋代没有左都御史这个官名。其次,即使泰兴是一个滨江的县份,沿江还有不少的沙滩,跨马渡江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泥马渡江,和宋代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太相似了,因此必然掺进了不可靠的成分。在这位宝明公之后又有十一官人、十二朝奉这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人物,不像历史的记载。此外,这部宗谱的首创者一冯公是明末的人物,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中间经历五百年,他凭什么写下这部宗谱?有一点明确的,是在满州入关以后,泰兴朱姓曾经搞起一支队伍,对于满洲人的统治,进行抵抗,这在《泰兴县志》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里都留下一些记载。
我的直系亲属,最远的我只记得曾祖父松年公,他住在江滨,因为他的耕地之旁,涨出几百亩沙滩,这一下他的情况大大好转,自己也搬到泰兴县城里来了,这就是苏家巷老宅,传到现在,我的侄儿还住在那里。可是长江是无情的,一场大潮,把松年公的沙田冲去了一大半。沙去了是无法挽回的,可是沙田已经升科,田租是轻易不能豁免的,他得从泰兴县到通州,一步步地去吁请,待到田租问题解决以后,他的沙田由于江水冲击和衙门使用,几乎全部报销了。
松年公只有一个儿子,即我的祖父星海公。因为早年境遇还好,他读了书,考过秀才,前前后后考过十次,始终没有考上。祖父还有一项本领,他是一位乳科的专家。家中相传,祖母是因乳痈致死的,这就使得祖父发愤专攻乳科,终于成为有名的专家。他的这门特长,后来传给我的伯父和父亲,伯父有时还为人家治病,父亲是一向不替人看病的。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只看到一些医书和成药,可能是父亲留下的,也可能是祖父留下的。可是由于伯父特别推重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相信父亲是一定学有专长的。
父亲石庵公兄弟二人,伯父玉山公也是读书的,考秀才好多次,可是也没有考到手。那时秀才只是一个口头的名称,正式的名称是县学生,通过这个考试,就算是县校的学生,可以受到教谕、训导——县校教师的官衔——的教育了。考试就是作八股,从《四书》里出题目,作破题、承题、起讲,以下便是八比,最后是一个小结。考试出身的称为正途,从县学生进而为举人、进士,这是一条做官的大道。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还有军功出身的一条路;直到清末,又有捐班出身,那更是鱼龙混杂了,都不及考试出身。严复从英国留学回来,重学八股,背着考篮入场;帝国主义分子赫德掌握了中国海关的全权,还要请人教他的孩子作八股,以便入场考试,都是这一回事。八股确实得到非常的重视。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十分可笑:那时入场考试,经常夹带舞弊,到今天还留下当时流行的不少书籍,密行细字,印刷的精致,远远超过现代书本,那时是一般人都可以置备的。还有些头童齿豁的老师宿儒,把全部《四书》都做成八股文,上千篇的文章都用小字密抄,编订成册,衬在考生常用的马褂里,这件衣服,有时要卖好几百元,考生买了,穿好人场,临时拆开照抄,同样可以考取。因此八股一途说可贵固然非常可贵,说好笑也就非常可笑。话说回来,我的这位伯父,虽在县考里曾经考到一名备取第一,在州考里却始终没有成功。
祖父和伯父一连遭到挫折以后,父亲当然不会考虑再走这条路了,他也知道自己是迟钝的,更不容选择这条道路。由于三姑母出嫁,最后一点点田地也作为妆奁田过了户,自己又结了婚,孩子也有了,总不能坐以待毙,最后下决心改业。恰好他的再从兄弟瑞二伯、长三伯两位正在经营一爿茶叶店,他就去那里担任售货员,从龙井、武彝、毛尖、雀舌这些货品里找出路,这样又经历了若干年。
可是这两位再从兄弟并不是什么经营能手,在倒闭的边缘上挣扎了几个反复以后,终于失败了。在这次失败中,父亲失业了,而且由于小小的县城里容不了几爿茶叶店,自己即使积累了些业务知识,竟然找不到第二个就业的机会。大的孩子总算在一家布庄当上艺徒,但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一家大小五口,吃饭就是一个问题,怎么办呢?父亲的心境正在煎熬之中。
就在这年十月的最后一个深夜里,我出世了,那年父亲、母亲都是四十一岁,大哥二十岁,二哥十二岁,三哥十岁。父亲正为家境的艰苦而困惑,大哥在店里,二哥、三哥都熟睡了。一盏昏暗的油灯投下深沉的阴影,产婆把婴孩收拾干净以后,包扎停匀,扔在方砖上给他第一次锻炼。
时间慢吞吞地消失了,曙光反映到这所朝北的小屋里,母亲从分娩的昏沉中苏醒过来,一眼看到躺在方砖上的婴孩,她挣扎着和父亲说:
“兴保爹,把孩子递给我,他在地下躺得太久了。”
兴保是大哥的小名,小地方的夫妇通常是带着孩子的小名相互称呼的。我在地上其实还只有半夜,由于母亲的慈悯,这才重新获得人间的温暖。当时的风俗是这样的,婴孩初生,要在方砖上躺这么一天一夜,据说为了孩子的健康起见,从小就得给他这样的锻炼。现在的办法完全不同了,不过我想这个办法不是没有道理,我能把我的健康情况作为一个具体的证明。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