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艺术思想的多重面貌:从艺术哲学到艺术社会学》:
齐美尔当然不否定理念可以或应当成为艺术的塑形对象,但他更强调,艺术自身价值的高低并不取决于理念,否则艺术随时面临被其他表现理念的形式取代的危机,理念的确有助于丰富艺术的内涵,但并不因此而成为人们评判艺术自身观赏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要地看看齐美尔是如何理解艺术品与真实/真理之间的关系的。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到此或许会按照某种惯性给出这样一种推理,即在齐美尔这里,“真”一定不能成为艺术品的终极目的,因为,这意味着艺术会被其他寻求“真”的形式取代,总之,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就只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目的,它是自为的存在。齐美尔的确认为,艺术只有作为“一个为自己而在的王国”才能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可这并不意味着齐美尔完全排斥了“真”成为艺术的某种目的。
齐美尔对艺术品和“真”的思考体现在他对自然主义艺术的研究中。早在1986年《社会学的美学》中,他就意识到了真、真实在艺术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艺术与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真实或现实以及自然截然不同,因为“一切艺术都改变我们自身原初的且自然地用以洞察真实的视域”,然而,他也承认:“尽管要成为艺术就只有超越直接的源自真实的印象之壤,但一切艺术都要从这直接的源自真实的印象之壤中汲取养分;艺术正是以一段内在的、无意识的反应进程为前提才能使我们确信艺术的真和重要性。”在此,齐美尔虽谈到艺术势必会超越真实,但同样的,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否定艺术与真实之间的关联。相反,他认为真实是艺术在展开塑形前必不可少的养分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也已经提出了“艺术的真”的问题,即无论怎样,“艺术的真”总要经过一个反映进程才能被呈现出来,这意味着它已然和现实世界中为艺术提供养分的那个原初的真实不同了。
相似的观点直到他在1913-1914年开设的艺术哲学的课程中还一再被提到,即“许多不被称作自然主义者的艺术家也像那些被我们称为自然主义者的艺术家一样仔细并深入地观察真实”。这就进一步说明,真实或者现实并非与艺术无关,相反,它们其实是许多艺术家开展艺术活动的前提。那么,自然主义艺术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齐美尔看来,它的问题显然不是对真实的观察或对真实的表现,而是对真实的过度接近,换言之,自然主义艺术,诚如齐美尔早就发觉的那样,“想用简单的形式摆脱与事物的距离,力求接近事物,直截了当地表述事物”,这种苛求自身精密地模仿客观事物的态度最终导致自然主义艺术势必会把那种近乎于科学的、理论的真当成艺术自身的目的,这不仅引发了艺术由此而丧失自身独立性的问题,还暴露出了自然主义者对艺术的真和理论的真的混淆,而这种混淆在齐美尔看来正是自然主义倾向得以出现在艺术中的主要原因,就此,齐美尔特别对艺术的真和理论的真进行了分别的澄清。在他看来,“理论的真是一切元素的协调一致,即一切元素和谐地凑集到我们的思考着的我的统一体中”,也就是说,客观事物的真最终涉及的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当自然主义者要求艺术去模仿客观事物以获得真实的时候,他所要求的不过是自身作为一个认识者去模仿他所感知到的认识对象而已;然而,艺术的真指的是“由作品申的一切可感部分构成的协调一致,这些可感部分构成的协调一致全都源自一个艺术家的心灵”,在此,虽然艺术的真看上去和理论的真一样都在达成一种统一或协调一致,但它们的细微差异在于,艺术的真涉及的并非艺术家作为认识主体同其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涉及艺术品和其表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只涉及艺术家,确切地说是艺术家的心灵和艺术品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每个经由艺术家的心灵而构成的统一的艺术品都可以因其作为“多样性的统一”而成为真,反之,所谓的“非真(Unwahrheit)”则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艺术家为那些可感部分提供了统摄它们的“一个心灵的根”。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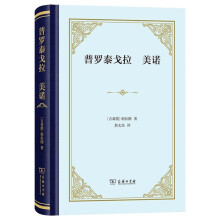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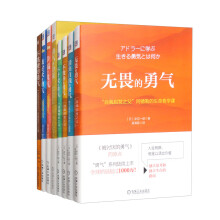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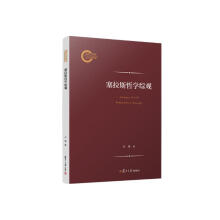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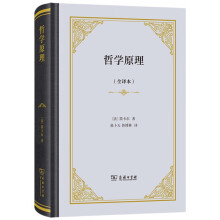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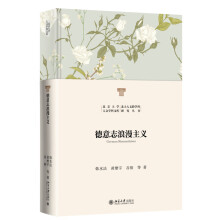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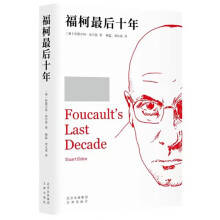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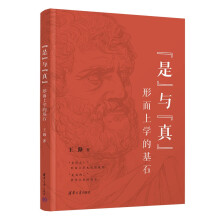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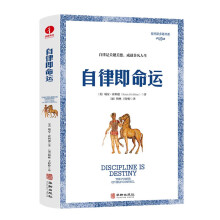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东教授
★《齐美尔艺术思想的多重面貌:从艺术哲学到艺术社会学》,较为深入地回顾和反思了德国社会学思想奠基人齐美尔的艺术思想。尤其是对齐美尔关于艺术与社会之关系的思想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学界所知不多的一些材料和有益的认识,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