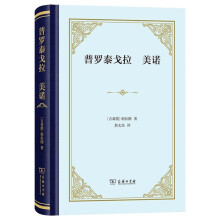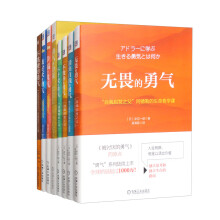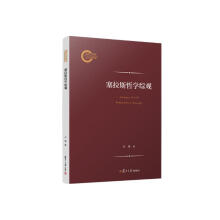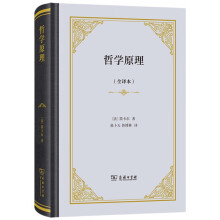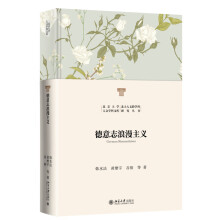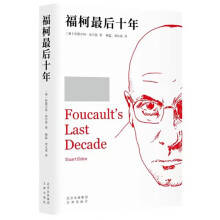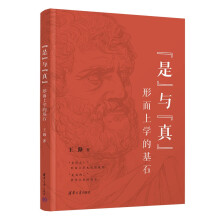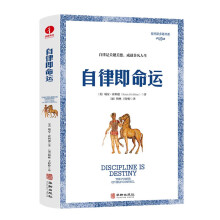《布尔迪厄文艺场域理论研究》:
正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民主、公平、合理的旗号高扬,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已经不再是赤裸裸的直接压制。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本质未曾改变,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方式却更加委婉、含蓄、隐蔽。
布尔迪厄围绕剥削方式的考察一直上溯到了古代/亚细亚的社会。通过观察古代/亚细亚社会的运作方式和经济特征,布尔迪厄揭示出“象征性资本”在社会中的产生、流通、消费、支配等的一系列状况,指出了支配者通过占有象征性资本而拥有施行象征性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名誉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不过,与“象征性资本”这一概念在本质上不同,“象征性暴力”则是要揭示出潜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提示出权力者通过掌握资本施行象征性暴力来实现对现存社会结构的社会再生产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象征性暴力”?这一概念突显了与直接人身暴力、经济暴力或物质暴力的区别,它是一种间接的、符号的、精神心智范畴的暴力。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语汇体系之中,他有时将“象征性暴力”与“象征性权力”互换使用。这一概念是其早年通过观察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社会的礼物交换所建构的象征性意涵而提炼出来的。在卡比尔这样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所谓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来规定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社会人的行为规范,也不存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府机关、法院、教学科研机构等正式的部门机构来明确社会人的社会等级位置。那么,卡比尔社会人是如何获得并施展象征性暴力的呢?一种主要的暴力方式是形成债务: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资金,债务人则由于借了对方的高利贷而必须服从债权人的任意支配。债权人的权力因向债务人直接提供经济资本而得以彰显,但是这属于一种硬性的权力,是外现性的暴力。
与之不同,另一种更为主要的暴力方式是软性的权力,内敛的暴力,比如通过赠送礼物实现。当社会人主动向另一方送出礼物时,另一方在接受馈赠的同时感受到“还情的压力”,所谓礼尚往来。尤其是当一方的礼物慷慨大方到另一方一时难以回赠的时候,受礼的一方就感到莫名的无形压力,受礼者为此将可以为送礼者做一切可能甚至不可能的事情。以此方式,送礼者使受礼者处于一种类似于负债、被支配、被占有的境地,处于被象征性权力施暴的状态中,即“象征性暴力”。这一类别的暴力被笼罩在诸如“情义、信任、义务、客气、忠诚”等崇高美德的美好面纱之下,当事人浑然不觉,因为它是无形的、文雅的、沉默的、不言而喻的。违规者可以不受法律追究,却会遭到良心的责备。
由此可见,布尔迪厄正是试图运用“象征性资本”“象征性权力”或“象征性暴力”等一系列象征性的因素,来揭示象征性资本的积累和分配正是凭借或推动象征性权力、象征性暴力的实施,使不平等的关系走向正当化、合法化的过程,并指出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关系温和的象征表象之下暗藏的非暴力再生的过程。
一般而言,“暴力”指涉社会统治方式和对立双方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方式,是通过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通过强制性的暴力行为实现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产生矛盾、斗争,最后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了社会的向前发展。可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一致,布尔迪厄亦赞同冲突斗争是社会运作过程中的不容忽视的重要特征,并指出“斗争是场域的根本特性”。不过,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涵不同,布尔迪厄认为不应该把社会主体的斗争还原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斗争,故他以场域为社会世界的基本点,指出在每个相对自主的场域内部,社会行动者主体皆是按照等级排列,场域运作的动力正是来自在场域之中处于不同位置、等级的行动者之间的竞争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的斗争首先是各个场域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这样一来,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法解释的所谓政治场域内部的斗争问题,布尔迪厄给予了一种明确的诠释,他站在一个发展的立场,揭示出由于政治领域内部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场域位置不同,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或隐或显的斗争的根本事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