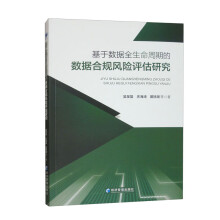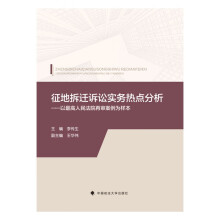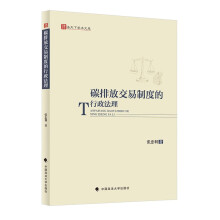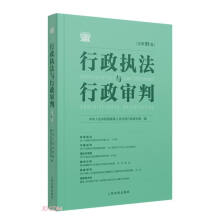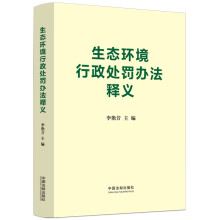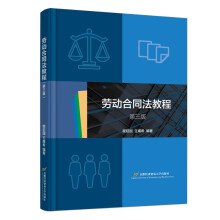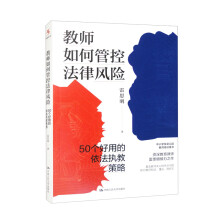《行政诉权研究》:
1.权利保护必要性之定位:起诉要件、诉讼要件抑或本案要件
权利保护必要性之定位既可能受一国立案制度所影响,也可能因行政诉权本质学说的不同立场而异。
首先,我国行政诉讼立案制度将权利保护必要性定位为起诉要件。起诉要件即诉讼开启的条件,其与诉讼要件、本案要件分别涉及诉的成立、合法与有理由三个层面,欠缺三者之一的结果依次为法院不予立案受理、不予实体审理、不支持原告诉求。新《行政诉讼法》第46条第2款规定,法院对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的诉讼“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56条第1款也规定,法院对违反复议前置的诉讼“不予立案”。这两处规定分别对应“不适时权利保护”中的起诉过晚与过早,均属权利保护必要性的范畴。换言之,权利保护必要性在此扮演了起诉要件的角色。
其次,有关行政诉权本质的实体裁判权说将权利保护必要性定位为诉讼要件。该学说又称本案判决请求权说,主张行政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作出实体审判的权利。无论法院最终是否支持原告诉求,均不影响其诉权的实现。依此学说,权利保护必要性与原告适格、行政纠纷可诉性一并组成诉讼上权利保护要件,而该要件又被诉讼要件所涵盖,故欠缺权利保护必要性即意味着诉不具有合法性,将由法院驳回起诉。
最后,有关行政诉权本质的具体诉权说将权利保护必要性定位为本案要件。该学说亦称权利保护请求权说,认为行政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对其作出有利裁判的权利;法院不仅有实体审判的义务,更有支持诉权人主张的义务。依此学说,权利保护必要性与原告适格、行政纠纷可诉性同属诉讼上权利保护要件的内容,其与实体上权利保护要件(即原告有关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或不存在之主张属实)并称权利保护要件。与实体裁判权说所不同,此处的诉讼上权利保护要件不能被诉讼要件所涵盖。欠缺权利保护要件中的任一种都将导致诉丧失理由具备性,也即权利保护必要性被纳入本案要件的范畴。
笔者认为,对于起诉要件之定位,考虑到其对行政诉讼“立案难”的化解不利,且缺乏对原告诉权保障的程序关怀,故不应支持。具体而言,权利保护必要性并非形式审查即可明辨,其与仅需形式核对起诉状有无必要记载事项的起诉要件不同。相比于后者的一目了然,权利保护必要性的查明工作潜在地要求法院作实质审查,否则无法完成任务。这便致使立案门槛被抬高,进而背离化解“立案难”的改革方向。又因上述实质审查发生在封闭化的立案阶段,一来本阶段完全交由法院依职权处理,二来被告尚未进入诉讼,两造对抗辩论的条件尚不具备,故原告还将面临程序保障阙如的困境。
至于诉讼要件与本案要件之定位何者更优,则取决于何者背后的诉权本质学说更有说服力。本案要件之定位缘于具体诉权说的立场。该学说以瓦赫提出“权利保护请求权”概念为诞生契机,经由赫尔维格的发扬而走向成熟。瓦赫认为,原告在起诉前就已存在要求法院作出有利判决的权利。①赫尔维格也主张,诉权即有权以诉的方式要求特定的、能够满足原告法律保护利益的判决。②该学说遭到彪罗的质疑,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利己判决请求权不可能在诉讼前就已存在,毋宁是诉讼审理终结时才出现,也即该学说误将权利产生的可能性当成了权利。③尽管瓦赫、赫尔维格均对此予以辩解,认为质疑者实则误解了具体诉权说的立场,并重申:彪罗混淆了诉权的存在与法院对其存在的确定,混淆了权利的存在和实现权利的可能性,还误将具有不确定性的权利当作无权;而原告宣称的诉权是否真正存在,需在诉讼中判断,也即诉的可能性仅是诉权不可或缺之前提,而非诉权本身。④然而,在笔者看来,上述辩解多少有些无力。尽管瓦赫、赫尔维格反复强调“诉前享有诉权”与“诉讼中经法院查明后享有真正诉权”的不矛盾性,并宣称诉权是满足特定条件下“有权以诉讼方式要求特定判决”、仅一方能够享有,但诉前尚不确定、仍待法院查明的“诉权”,又怎能称其“于诉前存在”呢?在一定程度上,这暴露出具体诉权说对“观念诉权”与“现实诉权”的混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