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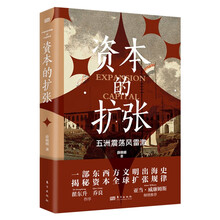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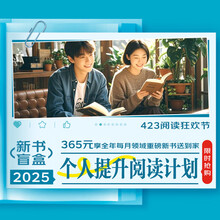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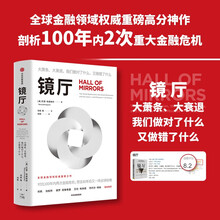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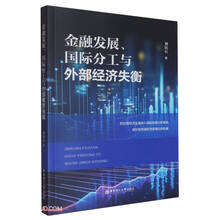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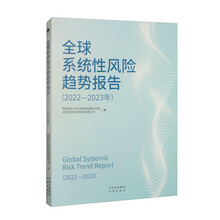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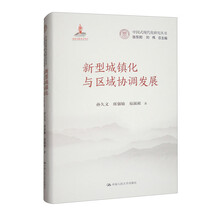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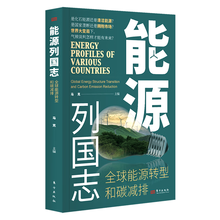



本书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详细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衰背后的原因,也讨论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主导下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作者揭示出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在1950年之后如何依靠着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的经济增长率而逐渐缩小。
纳亚尔笔触精妙,对“追赶”的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同时将其与尖锐的解读以及深刻的政策评论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对世界历史上这一重大过程独特的评价。尽管这种追赶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并不均衡,但这本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著作为我们展示了21世纪可能出现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彼时,全球范围内权力和财富都将实现更加平均的分配。
第9章
蕴含在过去里的未来
本书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所发生的演变,这种分析被置于广泛的历史背景当中,前后延伸了几个世纪,但是分析重点放在了20世纪中叶之后。第一部分是准备阶段。它研究了1820—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衰落与颓败。第二部分是重点。它分析了在1950—2010年所进行的追赶的程度和性质。本篇结语则负责总结。本章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大致给出了变化的轮廓,为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并概括出了一个未曾被人讲述过的故事的基本要点。本章第二部分从各种可能性和局限性出发,考察那些截至目前在追赶过程中领先的国家和那些可能会追随其后的国家的发展前景。第三部分则参考过去预测未来,并推测这种追赶将会如何重塑国际秩序,又或者会受到国际大环境怎样的影响。
1.变化的轮廓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区别是相对晚期才划分出来的。这种差异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逐渐浮出水面。事实上,1000年以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来,能占到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的80%。这里面主要的份额都是来自亚洲,而亚洲主要就是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它们两个就占到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的50%左右。这三个大洲在世界经济中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又延续了五个世纪,直到1500年。在16世纪早期至18世纪晚期,便能够察觉出这种变化的开端。航海大发现和对美洲的殖民是关键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在国家力量和海军力量的支持下,商业贸易实现了扩张。再加上欧洲发生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变革,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发展的初始环境。即便如此,在18世纪中叶,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相同点还是远远要比两者的差异更为显著。确实,人口、科技发展水平和制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可比性。18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接下来的50年里传播到了欧洲大陆,对即将发生的其他事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1820年,也就是不到两百年之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来还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三、世界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国和印度加起来所占的比重,在1820年的时候也超过了50%。
世界经济发生的颠覆性转变始于1820年左右。慢慢地,但是毫无疑问地,世界由原先的按地理划分逐渐转变为按经济划分。这种分类标准逐渐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重要性遭遇了急剧的下跌,以至于到了1950年,它们在世界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为三分之二,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四分之一,形成了如此显著的不平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820—1950年,欧洲、北美洲和日本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四分之一增长到了三分之一,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多一点增长到了接近四分之三。“西方国家”的崛起集中在西欧国家和北美洲国家。“其他国家”的衰落集中于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衰退,拉丁美洲是个例外,它在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的比重不仅一直保持平衡,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
人均收入方面出现的大分歧也的确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在短短的130年里,也即从1820到1950年,如果将西欧和西海岸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作为基数进行比对,拉丁美洲的人均GDP从占其五分之三降到了五分之二,非洲从占其三分之一降到了七分之一,亚洲则从占其二分之一降到了十分之一。但还不仅仅如此。在1830—1913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制造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其中亚洲的大部分,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产量从占比60%锐减至7.5%,而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主要是日本)所占的比重则从40%升到了92.5%,并且一直到1950年都保持着这一水平。19世纪发生的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亚洲国家的去工业化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就导致了大专项化的出现,也就意味着西欧国家及紧随其后的美国专门进行加工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则负责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1850—1950年的这一百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从而在国家之间产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劳动分工,导致发展结果极不平等。这一过程引发的结果就是亚洲的衰退和非洲的逆行。尽管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拉丁美洲除了在收入方面出现的分歧之外都要发展得比亚洲和非洲好一些,但是到了1950年,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依然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1950—2010年这六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和人均GDP水平占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比重所发生的变化展示出了明显的对比。以麦迪森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估测出的数据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960年之后停止下跌,这个时候的占比大约是四分之一,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迅速的增长,所以到2008年的时候占比几乎达到了二分之一;在人均GDP水平方面的分歧在1980年左右也告一段落,随后出现了适度的趋同,所以到了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占到了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水平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按照市场汇率下的当年价格为标准,在1970—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六分之一翻了一番,达到了三分之一,而它们的人均GDP水平占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比重也出现了些许增长,从十四分之一增长到了十一分之一。
GDP增长率方面存在的差异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和工业化国家所占比重的下降。在1951—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要比工业化国家的高一些。这一点很了不起,因为这30年也恰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候工业化国家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的增长率与之前100年里它们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这一增长率也比工业化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增长率要高。在1981—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几乎是工业化国家的两倍。198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都要比工业化国家低,主要是因为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率,但是在1980年之后,局势出现了逆转,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高出许多,而人口增长率又出现了减速。这些差别导致在1980年之后人均收入方面出现的分歧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适度的趋同,在1990年之后趋同开始体现出来,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就非常明显了。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在1950—1980年出现缩水,特别是与过去一段时间相比。但是在1980年之后又开始复苏,并在此后实现迅速增长。这种更深程度的参与是出于自愿的选择,与过去的被迫参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们在世界商品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翻了一倍多,从1970年的不到20%增长到了2010年的40%多。类似的,它们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也体现出它们在服务出口方面的相对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内外流量和存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现了增长,并取代了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份额,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作为目的地国而非资金来源国。人口从发展中国家迁移到工业化国家,这也成了一种重要的参与方式,尽管现在的移民法越来越严苛,领事实践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受到市场和全球化的驱动,人口迁移还出现了客籍工人、非法移民和专业人士的移民等新的形式。这种国际人口迁移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造成工业化国家生产力提高和经济活力增强的潜在因素之一。移民汇款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外源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它缓解了增长方面所出现的局限性,尽管人才流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负面结果,但是移民回流可以将其转变成为一种人才获得。
从1950年左右开始,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工业化进程方面出现了显著的追赶,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逐渐积蓄势能。生产总量和就业组成方面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导致农业所占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增长,这是出现上述追赶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在1970—2010年这四十年里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在不变价格标准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占其十二分之一,一举跃升到三分之一,在当年价格下,这一占比从八分之一一举跃升至五分之二。类似的,在当年价格标准下,它们在世界加工制造业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从十四分之一一举跃升到五分之二。
工业化还导致它们的贸易组成出现显著变化,初级产品和基于资源开发的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下降,加工制成品(特别是中等和高级技术含量的商品)在出口和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出现了增长。
……
历史也许不会重复,但是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是非常明智的。19世纪早期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转折点。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发生扭转。同时,欧洲,特别是英国逐渐在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早期是第二个转折点。英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告一段落。同时,美国崛起并主导世界。追赶和转变的过程延续了半个世纪。21世纪早期也许代表了一个类似的转折,美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可能会走向终结。北美洲和西欧之外的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亚洲的那些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世界中其他大洲的国家,一起构成了一种惊人的转变力量。亚洲的崛起和西欧的衰退,在相对而非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是可以察觉的。当与亚洲和西欧过去的历史进行对比的时候,这种逐渐显现出来的状况就多了一丝讽刺意味。
50年后的世界很可能是多极化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会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当然,对于未来“未来十四地”是否能继续崛起,那些紧随其后的国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发展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进行预测的,更谈不上预测的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一切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转变为包容性的社会,即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社会进步能够同时进行。这种追赶和转变如果能够实现,将延续至少半个世纪甚至更久。权力平衡的转变已经可以被察觉。过去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指示。
前 言
所有图例
所有表格
序言
第 1 章 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第一部分 / 渐渐落后
第 2 章 大分歧和大型专项化
第 3 章 潜在的问题与答案
第二部分 / 追赶
第 4 章 大分歧的终结 :趋同的开始?
第 5 章 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
第 6 章 工业化中的追赶
第 7 章 不平等的伙伴和不均衡的发展
第 8 章 逐渐出现的分歧 :不平等、排外和贫穷
结语
第 9 章 蕴含在过去里的未来
附录 :数据来源及其注释
注 释
参考文献
温馨提示:请使用员工书屋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