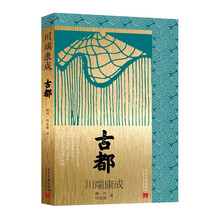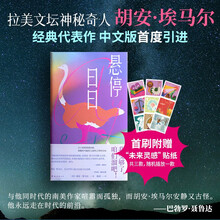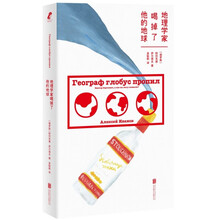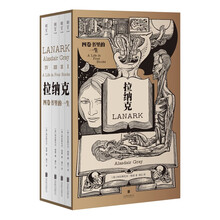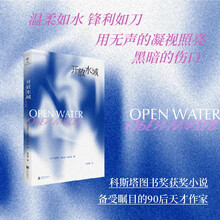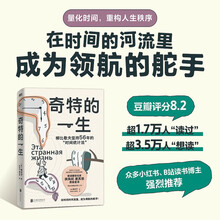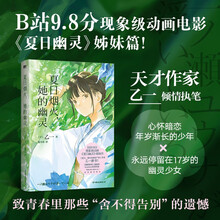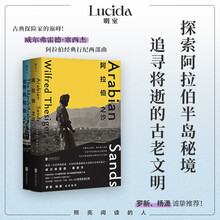《日本成长小说及其文化特性研究》:
之所以采用这一定义,首先是因为成长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成长小说文本也会存在文化特性上的差异,但都没有脱离欧美成长小说的原型或传统,因此,日本成长小说属于成长小说大类,并不需要一个新的、专门性的定义。其次是因为张教授的定义已经充分容纳了成长小说的自然流变过程,保留了成长小说最大公约数上的共性特征,且措辞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日本学者对成长小说的理解和界定。
加藤周一指出:“他(指福泽谕吉)的理想社会主要是19世纪中叶的英美中产阶级社会。在那里,国家(其象征是王冠或宪法)和个人的自由独立以及私有财产是神圣的。”②然而,日本并不真正具备这样的国情,因此,这种社会体制中产生的成长小说必然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张国龙给出的定义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笼统界定,倘要从浩瀚文本中筛选厘定出可归属于日本成长小说的文本,则有必要将这一范围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明确化。因为涉及成长主题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为数众多,若全部纳入成长小说的范畴则外延过宽。虽然成长小说必定要以成长主题为中心,但并非涉及成长主题的作品就可归于成长小说。鉴于此,《日本成长小说及其文化特性研究》拟从以下几个诗学特征来对日本成长小说进行定位,期待相关的文本判定和归纳能够较具有说服力。
(1)主人公具有积极的成长、发展意愿。一般而言,对自我或是处境的危机意识会引发“我是谁?”的哲学质询,成长正是从这种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出发,主人公会在对此问题有或明确或暖昧的意识的状态下,在一系列与己相关的事件中进行自我思考、自我教育、自我怀疑或自我肯定,这一成长过程通常较为漫长,自我身份需要被阶段性地进行确认,在达到成熟阶段之前,可能会经由“顿悟”而获得对世界和自我的具有认识飞跃性的洞察与体悟。
在日本成长小说中,主人公从最初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就会分化为两大类:“上升志向”型和“下降志向”型。其实,在“下降志向”型文本中,主人公对外界和自我内部的认识同样在不断深化,并且更为接近现代成长小说的特征。但就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这一类型的小说是否能划归于成长小说是具有相当大的争议的。倘若再对这一争议加以论述探讨的话,容易使《日本成长小说及其文化特性研究》有偏离主题之嫌,故而在选择文本时,将范围限定在主人公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相信人格的力量以及塑造人格的必要性的作品,并且,主人公无论是否获得世俗成功,都以各种方式化解了精神危机,自我没有走向崩溃。
(2)以主人公在性格或思想上的重要转变为主要成长向度。由于日本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个体存在差异,其成长阶段有可能不仅仅局限于青春期,为了保持对主人公成长阶段的整体关注,在文本筛选时不以成长期的物理时间跨度为标准,更不以生理成长作为“成长”的内涵。
不过,描述主人公个性转变、心理走向成熟的大部分文本在主题选择上往往并非以“成长”为唯一主题,很可能是多重主题,成长主题大多也不可避免地同情爱主题、青春创伤主题等交融在一起。只是,在成长小说中,成长主题必须居于主要的、鲜明的地位。诚然,人的性格、思想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是在青春文学中,主人公从头至尾基本不会表现出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重大性格转变,这是划分成长小说和青春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可以说,回溯与反思、经验与体悟是成长小说的重要标识。日本成长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在空间上的游历有所欠缺,但是其思想的重大转变却往往会改变原本的人生轨迹,成长的价值内涵即于此时得以彰显。
(3)以日本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与道德理想表达为中心。相较于西欧经典成长小说,日本成长小说缺乏社会理想建构,主人公注重对自己这一个体的“修身”。不过正因如此,日本成长小说与其他文类相比,作者会将自己的人格理想、价值观、道德理想寄托在主人公身上,或是经由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婉转暗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中亦可窥见作者如何看待“青春”和“成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