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近二十中国散文研究的重要著作,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修改而成。本书摆脱既有研究存在的散文本体论的桎梏,将现代散文的形成视为其在“现代”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文章”多重功能性持续削弱的产物,将近二十年散文的文体变革与写作内容的调整,视为散文逐步恢复其部分功能性的表现。以此为基,进入散文写什么、为什么这样写、怎样写与这样写的意义何在等切关散文本质的主要命题。
“底层”与知识精英的文学底层观
“底层”一词源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Gramsci)的 《 狱 中 札 记 》 , 在 曹 雪 雨 等 人 的 译 本 中 , 葛 兰 西 使 用 的“Subaltern Classes”被译成“下层阶级”“下层集团” 。葛兰西用“Subaltern”来意指欧洲社会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他的“底层阶级”主要指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底层研究虽属新兴课题,广涉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诸多方面,但“底层”本身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词语,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中,依据对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将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提出底层的主要来源是商业服务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在文学方面,20世纪90年代蔡翔的《底层》较早提出“底层”一词,具体指向在上海苏州河边棚户区靠体力劳动生存的工人 。“底层”作为一种直观的非历史概念,在西方有着两种社会分层观,一种是定性的阶级划分思路,以占有资源与不占有资源为人群划分,前者对后者进行压迫、剥削;另一种是定量的层化思路,即假定大家都占有资源,但有多少之别 。
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底层”实质上是一种革命力量的代言词,葛兰西从“底层”出发,将领导权的争夺从政治权、经济权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的概念涵盖被他扩展到包括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无业者等整个“市民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底层”关联着萨义德东方主义式的“他者”,但它不是后殖民主义指向的民族性“他者”,而是权力统治与一切占有资源的统治者的反衬,是一种近乎福柯权力对立物的观念,在美国还产生了包含人群更为广泛,甚至消弭了资源优势的“群众”概念。无论“底层”指向如何,但在世界的不同区域,占据社会基础的大多数人群——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者,实际上占据了“底层”所指的大多数。
“底层”的存在对文学表现现实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将“底层”视为一种身份概念,底层是被遮蔽的、模糊的、“消声”的。“底层”概念在中国知识界被迅速接受复制,意味着社会分层观在“底层”的模糊性中易于运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面向底层展露悲悯姿态的精英文学写作,与真正的底层始终有着审美的间隔。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持续的改革为知识精英提供了重新获取社会公共话语权的时机,一方面有着“士”“兼济天下”的历史传统,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事务的公民意识,拯济苍生般的高度社会参与与理想主义情怀不断膨胀。当这种急切改变现实的动力消退、责任感破灭之后,或陷入近乎“独善其身”式的现代犬儒主义,或产生借助“他物”别寻精神出路的遁世情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待遇、地位的调整与社会公共知识需求的增加,知识精英中的多数也成为改革获益者。 从积极的社会改革推动者、代言者到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文化资本占有者、经济上的中产阶层,当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社会定位的变动,与脱离乡土不同,底层很难唤醒人们的家园意识,更多地指向一种对于“启蒙”的解构。那些真正来源于底层而又并未刻意遗忘底层的作家如赵树理等人,对农民、底层游民、市民拥有一种深厚的阶层情感。无论是情感认同还是文化改写,当底层进入文学,它必须经历审美意识之维的转化,转向对审美形式、精神伦理问题的阐发。“底层”涵盖的广阔性,意味着底层经验的文学话语为各种话语的“杂糅”影响,难以以相对稳定的形态表现底层生活特别是他们心灵的苦难。
夏榆是否真的来自底层,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疑问。如同沈从文、艾芜等许多现代作家一样,夏榆、郑小琼等人的写作始终将本人的精神成长与生活漂泊联系在一起,不同形态的生活苦难带来了不同的书写意象。比如郑小琼的《铁》一文,将“铁”作为写作的核心元素。“铁”是生活、劳动的物质对象,也是吞噬工人手指的机器工业社会的象征。郑小琼说:“打工生活原本是一场酸雨,不断侵袭着我们的肉体、灵魂、理想、梦幻。” 她以“铁”见证、讲述、承担着打工生活的底层“忧思”。这种准确、形象的形象标志,在夏榆处更富于直接的象征性。“每天是8小时,有时候是12小时,有时候是16小时。我就那样坐在黑暗的矿井里,在巷道间,在石头垒砌的硐室里。” 在地底八百米深处,还有什么比矿难和矿工的生活更能象征底层的呢?面对长期的黑暗、频发的死亡、矿难与底层的暴力、悲伤,矿工夏榆感到,“在人的尘世生活的场景之下,在土地、河流、山脉、森林、草木之下是沉厚的漫无际涯的黑暗。我就是黑暗中的一粒尘埃”。
煤矿井下特殊的工作经历为夏榆的散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象征语言,它锐化了关于底层的经验过滤。大同煤矿井下的状貌、人的存在形态和特殊的地底灵魂体验,为他的散文提供了关系生命、潜在的不可知与人究竟应如何存在的思想动力。而那种普遍的“尘埃”感,正
是夏榆、郑小琼们在底层所感受的最常见的生存体验,夏榆富于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执着,意味着他与身处地底的“黑暗”形成了两种存在的对立。他自我描述说:“阅读对我而言已经不是学习和掌握知识,它是我消解在地腹中的孤寂的方式。”“而我在黑暗中,在一盏矿灯的映照之下阅读,我的姿态和形影就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稀有标本。我想是这样,我在阅读的时候为阅读本身心生感动。我觉得阅读的行为是我意识延伸的一个通道。我的意识穿行在两个世界。” 这种“通道”式的精神体验与现实生活构成了尖锐的崩力,令人质疑“幸福”模式的存在与存在的合理性。“底层”在夏榆笔下形成了多个层面的指向:现实生活的底层、煤矿自然的底层、精神生命的底层。“底层”作为精神维度的存在,不仅作为知识分子审美景观的“旁观”发现并存在着,而是以全景式视角验证了更广大的人的生活,展现苦难的日常与拔升的艰难。在人类精神的维度上,本无所谓“精英”抑或“底层”。底层的苦难伴随着命运感的蔓延,地腹的恐惧召唤着人类的精神解脱与宗教式的救赎感。夏榆散文展现着从个体到整体的底层呼喊,在他集中表现的“黑暗”中生发、壮大。“底层”与“黑暗”,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超脱性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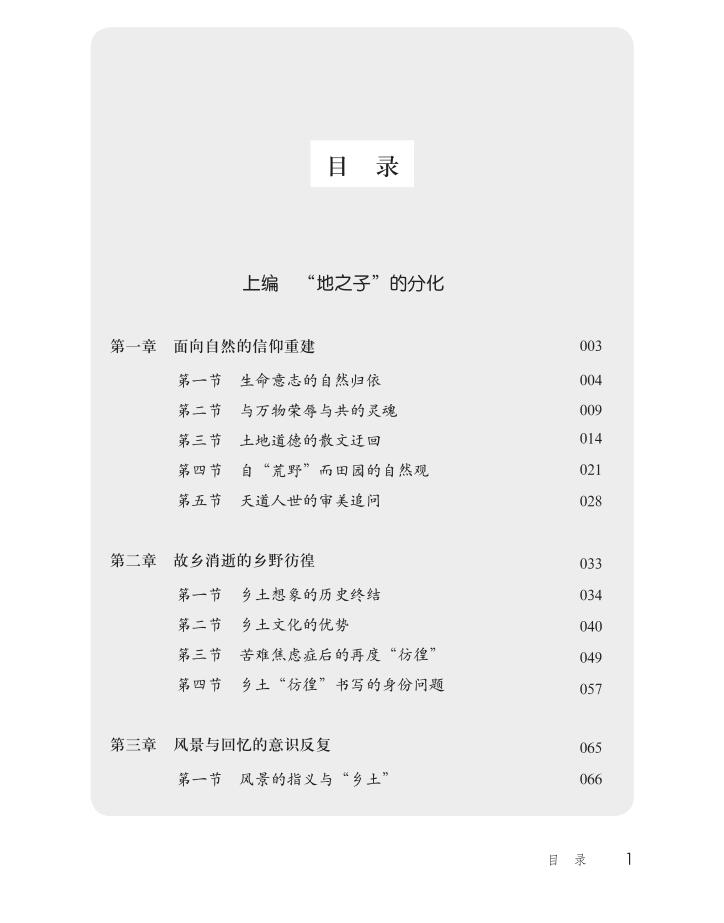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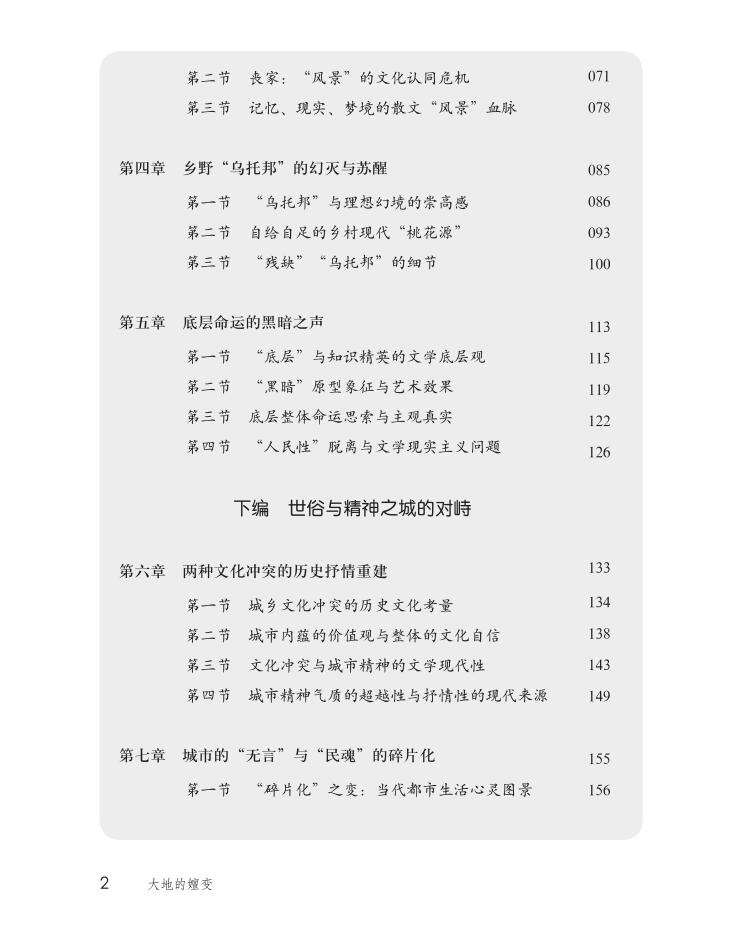

温馨提示:请使用员工书屋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