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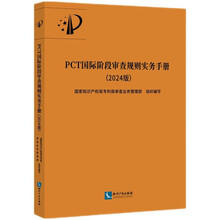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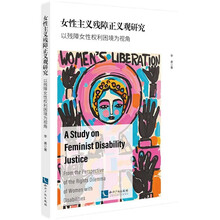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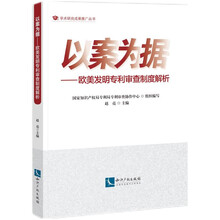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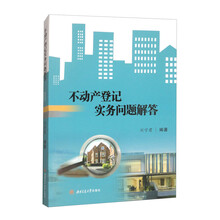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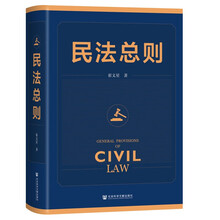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概述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保护客体论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基石范畴:损害赔偿抑或民事责任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构成要件
本书系作者对我国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研究成果集结。结合我国*新的民法典(草案)及有代表性的别国民法典,作者采用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联系刑法学、诉讼法学等相关学科,主要对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立法特征、制度价值、保护客体、*终基石范畴,及构成要件及其理论建构进行了阐述和深入解读。本书在内容上尽量吸收、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民法界的理论与实务相关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果。
第一节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外延与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前,我国学界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内涵与外延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作为国内侵权责任一般条款问题研究的先行者,张新宝教授认为,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居于侵权法的核心地位,而且应当是“作为一切侵权请求之基础的法律规范”。[1]根据此种观点,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在一国民法典侵权责任规定中居请求权基础地位,但凡侵权责任的构成与承担都需要经过该一般条款的检验,由于一般条款乃相对于所有侵权责任,所以可能继续下分为过错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等。另一种观点由杨立新教授主张,认为:“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就是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条款”,[2]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并不由侵权行为一般条款解决,而是由法律特别列举规定。不过,在《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后,二人的观点各有修正。由于《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2款对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人身、财产权益进行了例示性列举;第6条第1款规定了过错侵权的一般条款。杨立新教授据此认为,《侵权责任法》设置的是“大小搭配的双重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第2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法保护范围可以适用于全部侵权责任,因此可以作为大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第6条第1款只适用于过错侵权责任,所以是小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第2条第1款除了统率第6条第1款之外,还有第6条第2款“法律规定”的过错推定和第7条“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3]而张新宝教授则认为,“只有《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才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第2条第1款和第2款不过是一个宣示性规定,不是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不具有独立的裁判法的功能”。[4]
以上观点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外延问题,即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应当仅仅适用于过错侵权责任,还是应包括全部侵权责任;其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内涵问题,对此学者使用了不同概念,应厘清“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与“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侵权损害赔偿一般条款”为何种关系。对于第一个分歧,可以通过比较法考察予以澄清。而对于第二个分歧则需要揭示侵权行为、侵权责任,并需要对与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相类似的概念进行比较。
一、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外延:纵横考察
(一)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纵向考察
所谓纵向比较就是一种历史的考察,横向比较则主要是一种对当代国别立法的比较考察。通过纵向比较,我们可以明晰制度的源流与变化;而通过横向比较,我们可以揭示制度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
关于对制度的纵向或历史考察,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说:“如果我们通过任何立法,断定法律要领的早期形式,这将对我们有无限的价值。”[5]究其原因,梅因认为早期观念“可能含有法律在后来表现其自己的一切形式”。大陆法系的一般化立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法制史看,法对人的行为的调整经历了从个别调整到规范调整,从具体规范调整到抽象规范调整的过程。侵权责任法采用一般化的立法模式,也应当符合以上规律,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符合法律发展规律,也符合人类认识规律,它几乎贯穿了大陆法系侵权责任法从早期到现代的发展之路。对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发展进行分期研究,符合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杨立新教授将大陆法系侵权责任法一般化立法模式划分为古代法成文法时期、罗马法时期、法国法时期、德国法时期和埃塞俄比亚法时期。[6]这一概括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历史演进,描绘了人类抽象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但笔者认为,一般条款的发展脉络与民法的演进过程应当是一致的,无须进行过于烦琐的划分,况且近代民法中,法国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与德国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相比较,前者时间为1804年,后者为1896年,法国民法典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时间在先,但抽象水平更高。与民法的历史演进相适应,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直接区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即可。
1.古代法时期。从法律的发展来看,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主要是从具体侵权行为制度中抽象而来的,在一般条款取得侵权行为普遍规则形态之前,它更主要地表现为相互独立的具体侵权行为类型。欲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制度之本源,不能不考察各国早期的具体侵权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法并不能作为一般条款制度研究的起点。
侵权责任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复仇习惯。原始社会中,氏族组织和氏族习惯构成了调整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的两种基本力量。各民族均遵循类似路径,氏族内的纠纷绝大多数由当事人自行和解或依靠氏族首领的威望进行调解,部落公社末期,先是采取自由报复原则,即在本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时,部落其他成员均有代其复仇的义务,“由于实行自由报复可能漫无节制,后演变成了‘同态复仇’”。[7]整个原始社会的“侵权责任法”并不区分公私惩罚,野蛮的同态复仇遵循不成文的规则,属于团体对团体的复仇。
在早期的奴隶制法律中能够找到人们今天称为“侵权责任法”的诸多先迹。最初的损害赔偿只是一种可以用财物赔偿代替私人复仇的变通做法,但它体现了文明和进步,受害方和加害方之间不再复仇,而是以“赎罪金”代之,由行为人向受害方给付一定的金钱作为补偿,但该制度仍属于一种习惯,尚不具有法律意义,甚至仍有同态复仇的痕迹。在习惯演变为习惯法再发展成为成文法的长期过程中,自力救济逐渐被公力救济所替代,也为公犯与私犯的划分准备了条件,著名的公私法区分即是在罗马法公犯与私犯区分的基础上产生的。[8]当然,正如梅因所说,这只是“断定法律要领的早期形式”,罗马法列出了致害行为的受害人在具体情况下能够向责任人提出的各种诉权,“我们在习惯上认为专属于犯罪的罪行被完全认为是不法行为,并且不仅是盗窃,甚至凌辱和强盗,也被法学专家把它们和扰害、文字诽谤及口头诽谤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产生‘债’或是‘法锁’”。[9]侵权损害赔偿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人类社会进入成文法时期才得以确立的。在法律学的幼年时代,公民赖以保护使不受强暴或诈欺的,不是“犯罪法”而是“侵权行为法”,在古老国家的立法中,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一开始都是具体的,缺乏现代侵权法上类似一般条款这样的概括性、一般性条文。罗马法在大陆法系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其完善发达的程度令人惊异,其侵权责任法的有关理论也相当成熟,但即便如此,古罗马《十二表法》第8表的“私犯”专门对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对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仍采用个别列举的规范方式。个别调整方式和具体情况直接联系,针对性强但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在罗马法的后期发展阶段,偶尔的个别行为演变为比较常见的行为,个别调整也逐步进化为经常的、反复适用的、针对同一类行为的规范调整。有学者认为,“后期罗马法对侵权行为的一般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开启了大陆法系侵权责任法一般化的历史进程,这就是罗马法关于私犯和准私犯的规定”。[10]该学者认为,私犯与准私犯的划分基本对应现代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
笔者认为,规范调整的出现是法律最终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但从有关文献看,罗马法对于私犯与准私犯的划分,对于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仍仅具萌芽意义。优士丁尼时期将侵权行为划分为私犯和准私犯,首先,这种划分中的私犯与准私犯依然保留了浓厚的个别调整痕迹,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诸多赔偿请求的诉权,如窃盗、强盗、对财产的侵犯、对人身的侵犯等,[11]尚不是针对经常的、反复适用的某类行为;其次,这种区分纯粹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不是自觉完成的、践行制度的文明之举,因为罗马法“规定在前的称私犯,规定在后的称准私犯”[12],并没有对私犯或准私犯进行抽象和概括以提炼出包含一切侵权行为和准侵权行为基本要件的一般条款。所以,私犯与准私犯的划分并不像有的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决定了现代侵权责任法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的分野,也不能构成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依据。
罗马法中私犯与准私犯的划分,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仍摆脱不了偶然性和任意性,它虽然对各类侵权行为及其造成的侵权责任都予以了详细规定,但并未给处于该类行为领域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提供明确的一般化行为模式,基本没有将侵权责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先例。因此,有罗马法学者指出:“古罗马关于私犯的法,同它的契约法一样,没有什么一般原则。这种关于私犯的法设计的都是具体的错误。不过,有两种私犯形式以其概括性而引人注目,这就是侮辱和非法侵害。以此为基础,民法法系建立起关于民事侵权的一般理论。”[13]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说罗马法中私犯与准私犯的划分对于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产生具有萌芽意义,没有必要在古代时期进行前罗马法与后罗马法时期的再划分。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形成是近代侵权责任法立法与理论发展的产物。
2.近代法时期。近代民法,“是市民社会里规定私人相互之间关系的法”。[14]也有学者将其时间段限定为“经过十七八世纪的发展,到达十九世纪”,范围包括“德、法、瑞、奥、日本及旧中国民法等大陆法系民法”,“也包括英美法系民法”,以上各国“因编纂民法典而获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的体系”。[15]但对于侵权责任一般条款问题,因为英美法系主要采用了类型化的立法模式,本文不予涉及。在大陆法系近代民法中,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两者在时间上相差大约百年,但在抽象化程度、保护范围和立法技术、价值趋向上各有不同,并依然深刻影响着现代各国的民法典编纂和司法实务。
1804年《法国民法典》诞生,标志着侵权责任法真正转入一般条款阶段,它继承了罗马法对私犯与准私犯的划分,将私犯改造为加害行为,并在准私犯的基础上发展出准侵权行为。但是在对《法国民法典》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理论识别上,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法国民法典》关于侵权之债的规定主要有五个条文(后经修正后第1384条增加到多款),与一般条款识别有关的仅涉及其中三个条文,分别是:[16]
第1382条:人的任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该行为发生之人应当赔偿损害。
第1383条:任何人不仅因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且还因其懈怠或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第1384条第1款:任何人不仅因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且对应由其负责之人的行为或由其照管之物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本文前述的对于一般条款识别上的差异在第1384条第1款上显现了出来。张新宝教授将以上三个条款均认定为一般条款,“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所有侵权行为和准侵权行为的最重要的要件,而且构成了一切侵权请求的基础:在此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诉因”。[17]杨立新教授则将第1384条第1款排除在一般条款之外,“《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第1383条才是真正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这是将侵权行为作了最大限度概括的一般化条文”。[18]
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可能更为可取,因为“一般条款,指称的就是概括一般侵权行为的条款,准侵权行为是列举在该条款之外的”。[19]欧洲著名侵权法专家冯·巴尔教授的观点印证了这一认识,他认为第1382条和第1383条规定了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三个构成要件,“基本规则变成了一个一般条款,并从那时起,法国法院就不得不从这一规定开始发展基于过错责任的民事责任法”。[20]虽然第1382条和第1383条都是关于自己责任(过错责任)的规定,但前者涉及故意侵权责任,后者涉及过失(疏忽)侵权责任,二者结合为一个完整的侵权责任的一般
条款。[21]
德国制定的民法典走的同样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道路。对于这一点有学者并不认同,论据是德国法系按照“类型”确定侵权责任构成,此非“一般”的条款。实际上,《德国民法典》对侵权责任的规定采取一般条款模式在比较法学界认识相对一致,所不同的是,德国模式不同于法国,兼采概括列举和递进补充来区分权利和法益。德国法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被浓缩于第823条、第826条中,分别被概括为“权利侵害”“违反保护性规定”和“故意违背善良风俗”,同样仅规范了一般侵权责任。这样,《德国民法典》就将“各种诉因类型化”,“而欧洲其他国家都是跟着《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将其糅合在一条统一的一般条款中”。[22]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除了行为人的过失以及损害外,是否还需要另外一个表现客观要素的要件呢?比较法上对于此问题,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两种路径,并作为法国和德国模式的区别:其一,只要行为人有过失,任何损害都将产生责任(“不害他人”原则);其二,“禁止损害他人”的规则只适用于典型的和特定的情形(“不法的典型性”规则)。[23]笔者认为,法国法由于对权利与法益不加区分,导致救济的闸门开得太大,而德国法区分权利和法益,类型化的救济模式导致有时闸门开得太小,两个国家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任务就是吸收对方模式的合理因素,促进自己的发展。
3.现代时期。进入20世纪,欧洲各国民事立法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问题上,或侧重法国模式(如意大利),或侧重德国模式(如希腊、葡萄牙等),不过总体趋势是在两种模式之间吸收对方的合理因素寻求妥协,具有折中主义的色彩。“在法律适用上,一般条款经历了从普遍适用到限制适用再到重新获得重视的过程”。[24]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法系侵权责任立法有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在非洲新兴民族国家意识到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后,一般条款在向概括性加强的方向发展,不仅涵盖一般侵权责任,而且同时涵盖特殊侵权责任;其次,在20世纪末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律统一运动促使一批学者兼收两大法系(英国和法德)和大陆法系两大代表(法、德)制度中的各自优势,对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进行了新的探索,这种现象值得重视。[25]
比较法上的典型例子,1960年制定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是“法国人的变革法典的被压抑的热情”与“埃塞俄比亚人的求新法于西方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愿望”两股改革热情碰撞的产物。[26]其第2027条规定了三个一般条款,第1款针对的是加害行为:“任何人应对因过犯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不论他为自己设定的责任如何”,从这一款规定中我们看到了《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第1383条的影子,第2款针对的是“物件致损”,“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形,一个人应对因其从事的活动或所占有的物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以上在《法国民法典》中属于准侵权行为;第3款则规定了“替代责任”,“如果某人根据法律应对第三人负责,他应对该第三人因过犯或依法律规定发生的责任负责”,在法国法中,替代责任也属于准侵权行为范畴。从大框架看,以上条文依然延续了《法国民法典》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的区分并依此确立侵权责任立法的条文框架,而在内容上不仅涵盖了一般侵权责任(第1款),还涵盖了特殊侵权责任(物件致损与替代责任等准侵权行为所生责任),概括的是全部侵权行为而非仅限于过错侵权行为。
[1]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张新宝:“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 杨立新:“论侵权行为一般化和类型化及其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模式的选择”,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 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五版)(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124页。
[4] 参见张新宝:《走过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77页。
[5]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页。
[6]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五版)(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118页。
[7] 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43页。
[8] 施玮、叶成朋:“大陆法侵权行为法之古代状态”,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9]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8页。
[10]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五版)(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11] 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债·私犯之债(II)和犯罪》,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 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66页。
[13] [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二版),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关于私犯与准私犯的划分为什么不能与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区分相等同,其讨论可以参看该书第240-241页。
[14] 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增补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5] 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6] 《法国民法典》(下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3、1096页。
[17]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载氏著:《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18] 杨立新:“论侵权行为一般化和类型化及其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模式的选择”,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9] 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概念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狭义上的,如法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标题“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仅指称“一般侵权行为”,即过错侵权行为;一种是广义上的,它既包括侵权行为(过错侵权)也包括准侵权行为(替代责任与物件侵权行为)。杨立新教授从法国民法典的标题中推导出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应当是过错侵权的一般条款,实际上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这种推导方式并不恰当。
[20]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1]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在法国民法典第1383条中,其所宣称的法律内容是,一个人不仅对故意行为(民法典第1382条)承担责任,而且对由于他或她的过失或疏于注意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关于法国民法典规定的侵权责任依据问题,另可参见张民安:《法国侵权责任根据研究》,载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以下。
[22]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3] [意]罗道尔夫·萨科:《比较法导论》,费安玲、刘家安、贾婉婷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2页。
[24] 意大利学者就意大利民法典中一般条款的适用和立法技术指出,一般条款在意大利经历了从普遍适用到限制适用再到重新获得重视的过程。欧洲统一法进程为一般条款重回历史舞台提供了机遇,法院在此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叶微娜、胡小倩:“‘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5] 从《欧洲侵权法原则》、《瑞士侵权责任法草案》、《法国债法改革侵权责任法草案》、德国侵权责任法改革动议乃至我国台湾地区“侵权责任法”修订工作来看,特殊侵权(危险责任)一般条款模式受到重视。参见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上册 侵权成立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412页。
[26] 参见徐国栋:“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两股改革热情碰撞的结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第一章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概述
第一节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外延与内涵 003
一、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外延:纵横考察/ 005
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内涵/ 018
第二节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立法特征与价值 027
一、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立法特征/ 028
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目的价值/ 032
三、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形式价值/ 041
第三节 小结 053
第二章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保护客体论
第一节 一般条款保护之客体范围——权利与法益 059
一、权利与利益之界定/ 060
二、权利与法益区分之实益/ 072
第二节 一般条款对客体保护之进路 081
一、权利/ 082
二、应当权利化之法益/ 096
三、不能权利化之法益/ 113
第三节 小结 127
第三章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基石范畴:损害赔偿抑或民事责任
第一节 一般条款基石范畴之前提——民事责任、义务与债之关系厘定 135
一、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 135
二、民事责任与债/ 138
第二节 一般条款基石范畴之证成——以侵权责任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功能比较为中心 146
一、侵权统一救济模式之批判/ 147
二、侵权责任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竞合模式之批判/ 162
三、侵权责任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并立模式之合理性/ 169
第三节 一般条款基石范畴之制度配套——绝对权请求权 183
一、人格权请求权之建立/ 184
二、知识产权请求权之建立/ 189
三、其他绝对权请求权存在性之探讨/ 195
第四节 小结 201
第四章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构成要件
第一节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构成要件理论 207
一、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构成要件之比较法考察/ 207
二、我国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构成要件理论/ 212
三、“三阶层体系”理论及其运用/ 217
第二节 要件符合性 226
一、要件符合性及其判断之性质/ 226
二、加害行为/ 228
三、侵害权益/ 234
四、责任成立之因果关系/ 240
第三节 违法性 247
一、违法性要件之必要性分析/ 247
二、违法性之分类/ 255
三、违法性之认定:结果不法说与行为不法说/ 257
四、违法性要件之实务态度与运用/ 267
第四节 有责性 273
一、过错/ 273
二、侵权责任能力/ 275
第五节 小结 278
结论 279
参考文献 283
后记 303
温馨提示:请使用员工书屋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