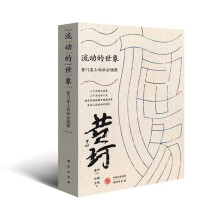革命的社会观
当我们比较一下研究不列颠政治、帝国以及政治思想的历史学家们所持有的新观点时,就会发现某些矛盾。举例来说,我们怎么能强调一个为地方集团控制的政府的帝国远见呢?在把这些新观点协调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以前,我们只能探讨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相对重要性。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就是:这些新观点都要求我们重新考察诸如为什么竟然会爆发革命的问题。假如航海条例是公平的,假如美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执着于任何关于议会权威的特定观点,假如乔治三世不是暴君,那么,为什么殖民地人民还要追求独立呢?另外,革命又是什么呢?假如班克罗夫特的答案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将用什么样的答案来代替它呢?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最使历史学家们满意的似乎是卡尔·贝克尔所提出的答案了。他在《一七六〇—一七七六年间纽约殖民地各政党的历史》一书中指出,革命期间纽约的政治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地方自治和谁应该治理本地大家都知道这场革命是为了获得地方自治而进行的,换言之,就是为了独立。贝克尔的论述以及他著作的要旨都使人们注意(与独立战争)同时发生的殖民地居民自身之间的冲突。纽约也许是贝克尔能够阐述自己观点的最好的地方了。就像后来欧文·马克的一项研究(《殖民地时期纽约的土地斗争,一七一一—一七七五年》)证明的那样:革命前,殖民地政府被一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贵族所控制总督的政务会、殖民地议会、法院以至律师界都挤满了拥有大地产的人们或他们的亲属,这些大地产所有者在哈得逊河谷和康涅狄格河谷北部往往拥有十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尽管贝克尔没有统计资料证明这类事实,他还是相信纽约反对不列颠的征税和民众反对当地的统治阶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初,这些大人物带头唤醒了人民抵制不列颠的征税(可能因为他们从中看透了征税是对他们地方控制权的一种威胁)。但是,由印花条例引起的骚动,证明了这些贵族怕人民大众的程度可能甚于怕英国的控制。因此,他们从反英的行列中撤退出来,并且也试图使人民默许征税。但实施这个计划的时运不佳,印花税条例的骚动已使一批民众领袖涌现出来,他们是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在保守的贵族有把握地控制下的地方议会是够顺从的了,然而一些超出法律管辖范围的委员会仍然继续出现,坚持与英格兰相敌对。虽然,这些保守的贵族也常常加入这些委员会,并竭力想保持对它们的控制,但他们最终面对着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成为效忠派,或者和人民革命团体共命运。他们之中许多人,如约翰·杰伊、詹姆斯·杜安,都参加了革命,并保持了充分的领导地位,进而把一部保守的宪法强加于这个新生的国家。在以后的十年中,纽约的历史表明,在胜利的革命者之间,即以原先统治阶级的成员为一方和以小农为另一方之间展开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贝克尔既没有主张纽约的革命仅仅是社会内部的两个阶级的斗争,也没有证明其他殖民地必然发生类似纽约的情况。以后的历史学家却多少把他的解释推进了一步。阿瑟·迈耶·施莱辛格在《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一书中,研究了所有殖民地商人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十二年动乱中的作用他发现,在最初反对食糖税条例和印花税条例当中,商人起了领导作用。不过,印花税条例引起的骚动使他们停顿下来。当汤森德条例获得通过后,他们再度采取不进口公约的手段,但却表示坚决反对暴力。当下层各阶级对不进口公约满怀热情时,这些商人却逐渐不那么热情了。一七七〇年以后,他们竭力想把下层阶级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防止与英格兰的敌对行动的爆发。仅当茶叶条例威胁到他们,把他们从茶叶生意中排挤出去时,他们才决心再次站出来带头反对不列颠。他们反对的结果是场大灾难,以至于他们许多人很快地退缩了。但是为时已晚。施莱辛格教授以独立的来临作为他叙述的终结,不过,在最后一章里,他展望了战争和战后的一些年代,看出了商人和贵族一起仍然和那些在这场革命的鼓动中变得突出的上述下层阶级进行尖锐的对抗。贝克尔和施莱辛格两人写的都是有关革命时期的一些特殊的发展,贝克尔写的是关于纽约的政治,施莱辛格写的则是关于整个殖民地的商人。J·富兰克林·詹姆森的著述则把整个革命看成是一场民主的剧变,它的开端可能仅仅是一次政治抗议,反对英国议会的那些条例,但接着以像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同样方式广泛展开,从而改造了整个社会。詹姆森说:“革命的激流,一旦形成,就不可能被限制在狭窄的堤坝之间,必然广泛地扩展到陆地上来。”同时,他探查了众多的社会变化中的滚滚洪流,所有的变化都“趋向于一种均衡的民主制这个方向”。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在许多州的废除,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财产权的废除,效忠派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选举财产资格限制的降低,政府对英国国教的支持的废除——在这些以及相类似的发展中,詹姆森看清了谁应该在本地进行统治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正像贝克尔、施莱辛格、詹姆森所表述的那样:从社会观点来观察这个革命,就把殖民地人民自身的斗争夸大到最大限度,从而趋向于把殖民地与英格兰之间的斗争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看到了殖民地居民之间所以互相厌恶的原因,可是,他们为什么对英格兰如此愤怒却很少被明确地揭示出来。宣传可能是一个答案。有三本重要的著作已经探讨了用宣传方式导致民众敌视母国这一问题。在《萨姆·亚当斯:宣传工作的先锋》一书中,约翰·查斯特·米勒描述了一个人如何通过促成叛乱爆发的重大事件来领导马萨诸塞居民。菲力普·戴维森在《宣传与美国革命》中指出了其他一些鼓动家和他们组成的团体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利用全部殖民地的公众感情的。施莱辛格教授在《独立的序曲》中,对一些报纸和它们的出版商的作用这一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研究。这些书都包含了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宣传”一词已经失去了它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前所具有的魅力。我们甚至再也不能自信,说我们懂得宣传的意思是什么。(真理能是宣传吗?或者宣传往往是虚假的吗?)然而,仍然存在着一种看法,即就其为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而言,这场革命是由于像萨姆·亚当斯和帕特里克·亨利那样的鼓动家的努力而产生的,而他们却夸大了英国的罪过以便达到自己特殊的目的。对邦联与宪法所做的经济的与社会的解释这很难算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帝国学派和社会经济学派的历史学家们都还依赖于这个答案,他们对于寻求一个更好的答案都不太感兴趣。虽然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即美国革命是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这一命题还没有在对这个时期的任何深入研究中得到证明。实际上,那些强调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历史学家较少涉及殖民地敌视英国的原因,而谈论较多的则是后来的社会分裂的历史,贝克尔和施莱辛格都阐述过独立之前一段岁月这种社会分裂的历史。这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下述问题:那些殖民地内原有的统治阶级遭到过什么情况?他们是否被彻底推翻,因而导致新的美国各州完全地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所统治?由阿伦·内文斯和最近伊莱沙·道格拉斯先后对新生的州政府所做的两项概括的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原有的统治阶级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没有被彻底地更换。尽管新州政府可以比旧政府给予下层阶级更多的好处,但是富人和出身显贵的人仍在继续发挥其强有力的影响。接着,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同该世纪七十年代一样,阶级与阶级之间旗鼓相当,互相对阵,每一个阶级都企图控制政府。因此,社会分裂就像在《独立宣言》发表以前一样,也可以当作了解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以后这一段历史的钥匙。关于这一点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读查尔斯·比尔德所写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九一三年版)一书,它是所有撰写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比尔德的书是继贝克尔的研究之后不久出版的,虽然此书并没有涉及革命的本身,但它也许比贝克尔的书谈论更多的是劝告历史学家,必须用阶级冲突的观点来观察美国革命的全过程。比尔德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的五十五名成员逐个地进行审查(比尔德在运用这种历史调查的方法方面先于纳米尔)。根据财政部的档案,比尔德能够证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握有公债券,它们作为新宪法的一项成果而提高了价格。他们通过强化政府和提高合众国的信用使他们对政府公债的投资得到了偿还。他们也许是按照对他们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的假设行事的,但是比尔德指出,这些人当时并没有投资于不动产,而是投资于动产;他们制定宪法就是为了保护动产的安全;而他们之所以能使这部宪法获得通过,仅仅是因为大多数居民没有参加投票。这样,从比尔德的研究来看,那些开国元勋们是作为一个有才干的资本家投机商集团出现的。他们成功地哄骗了一般平民百姓去接受一个以有利于少数显贵们为目的而设计的政体。比尔德所说的一些动产所有者就是阿瑟·施莱辛格提到的那些商人以及卡尔·贝克尔提到的那些纽约贵族在经济方面的后裔,或者也可能就是他们本人(从“独立宣言”到制宪会议只有十一年),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如果比尔德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似乎是那些在一七七六年失去了控制权但还有影响的贵族在一七八九年又夺回了全部的权力。
上述结论是梅里尔·詹森在对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两项研究中加以详细说明的。较早期的一些著作把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看作是前途暗淡的时期。那时,取得战争胜利的美国人由于地方之间的争吵和妒忌的危害而处于危险局面。约翰·菲斯克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把这个时期称作“危险时期”。他在这本书中指出美国正处在瓦解状态,无力提抗外侮,它的商业和贸易都衰退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缺少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其他的历史学家们都已认识到,菲斯克描绘的这幅图景并不完全准确,而詹森则在《邦联条款》和《新国家》两本书中都正面批驳了菲斯克的观点。詹森论证说,“邦联条款”是“独立宣言”原则的政治体现,而“独立宣言”则是民主革命的体现,这次革命既反对地方贵族统治,又反对英国。在根据《邦联条款》产生的国家实体的整个时期里,那些保守的贵族们时刻都阴谋重建大不列颠先前曾竭力建立的那种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如果说这个时期存在着危险,那也是由这些“勉强的革命者”造成的。但是,不管怎样说,这个时期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糟糕。由各州设立的地方关税一般说来是针对外国的,而不是针对邦联其他成员的。美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是当时整个欧洲局势的结果,并不是美国的软弱造成的。在废弃邦联条款以前,美国的经济繁荣已经开始出现了,而贵族们所真正厌恶的则是这个时期的民主制度。这样,从不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于从一七六三年到一七八九年整个时期的一致的解释。其首要的论题就是阶级冲突以及谁将在国内进行统治的问题。在独立之前的动乱时期,群众被发动起来去反对被信以为真的英国暴政,但是群众发现了另外一些更加显而易见的当地暴政,从而对之发泄了他们的愤怒情绪。随着独立的到来,群众就设法谋求多方面的改革以争取更加广泛的民主制度。但是,那些保守的财产占有者和资本家投机商们却千方百计紧握权力不撒手,他们终于随着宪法的正式通过占了上风。这种解释是由几个不同的互相呼应的研究部分构成的,因而引人注目。这种从整个历史时期做出的解释是有意义的,甚至指出了对美国历史的其他阶段探求相类似解释的方法,那就是把美国历史的其他阶段看成是反对上层阶级专制主义的渴望民主的解释的方法,那就是历史。这种解释企望把一八〇〇年杰斐逊派的革命,杰克逊的民主制以及平民主义、进步主义、新政等都看作是“七六年精神”的化身,而把联邦主义者、辉格党人、内战后的共和党人等都看作是复活了的贵族统治的代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