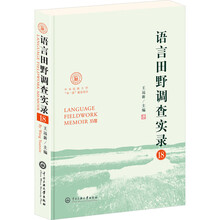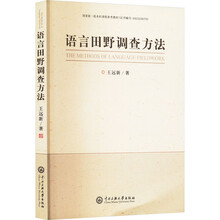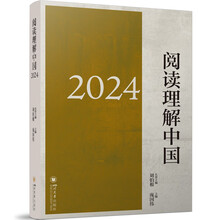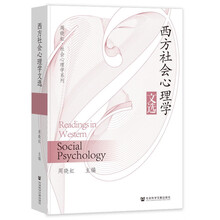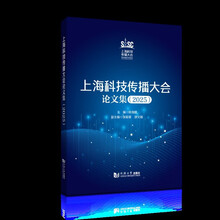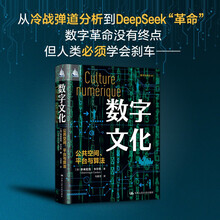《焦点的澄明:牟宗三儒学思想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这样就引出了康德的道德自律学说。康德指出:“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律和与之相符合的义务的惟一原则;反之,任意的一切他律不仅根本不建立任何责任,而且反倒与责任的原则和意志的德性相对立。”康德认为,德性的唯一原则就在于它可以不受一切经验质料的影响而完全独立,而且可以通过单纯的立法形式来决定意志。这就牵涉到了在康德哲学中居于拱心石地位的自由概念。康德将自由分为消极意义的和积极意义的两种。所谓消极意义的自由即是独立于自然因果关系的自由,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可以不受一切质料的影响而完全独立”;所谓积极意义的自由,就是理性为自己立法,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通过单纯的立法形式来决定意志”。积极意义的自由也就是自律。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也就是自由的自律,这种自律本身就是一切准则的形式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一切准则才能与最高的实践法则相一致。
“自律”一词,原本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意指一个政治团体乃至国家为自己制定法律并依法律行动的权利。在一个政治团体中,个体必须服从这个团体制定的法律,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自由,这显然是一种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卢梭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一个共和国的法律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共和国接纳每一个成员,将其作为全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必须将自己置于共同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这样,共和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双重身份:即是主权者中的一个分子,又是服从者中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说,在卢梭的共和国理想中,每一个成员透过社会契约而成为主权者的一个分子,同时又都有义务以臣民的身份服从由共同意志制定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与服从的矛盾就解决了:共和国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自由的,他服从的法律其实是自己制定的,并未受到外来意志的限制。
康德借用卢梭的共和国模式,将自律的概念引入其道德学说,对于说明道德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康德看来,人既是感性的存在者,有感官的欲望,受自然因果规律的制约,因而是不自由的。但与此同时,人又是理性的存在者,可以完全独立于一切感性条件的制约,有绝对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可以制定法则,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是说,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可以自己给自己立法,而不受外部自然界的控制。在这种理论格局下,恰如卢梭的共和国一样,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人们服从的立法完全是自己制定的,并非受制于外在的影响,而且由于自己就是立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是自觉自愿,甘愿如此的。道德自律的理论使康德的道德理论与以往一切道德理论有了原则性的区别。在康德看来,以往的一切道德理论尽管有内在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幸福论基础上的,因而都是道德他律。这些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或是诉诸经验主义原则,或是诉诸人性的特殊结构,或是诉诸神学概念,没有把道德建立在理性的根基之上.没有让主体通过理性为自己立法,结果不仅没有把人引向道德,反而更加远离了道德。与这些理论相反,他坚持认为,只有让理性自我立法,才是道德最可靠的根据,才是通向道德最正确的途径。一言以蔽之,道德自律就是理性自我立法、自我服从,排除一切质料原则的道德学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