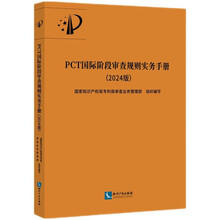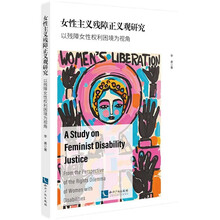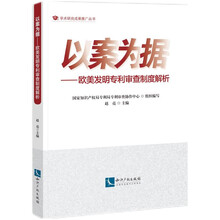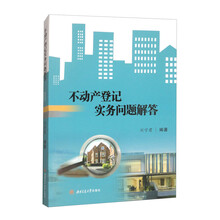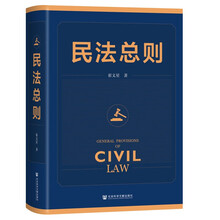《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
(三)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之评析
从上述分析来看,正是因为现行法律关于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构建过于概括性、原则性,因缺乏明确可行的具体操作流程,以致司法实践中关于成年人意定监护的纠纷少之又少,但现实状况又急需适用。因此,对监护制度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新梳理,使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实现与现有监护制度的良好对接迫在眉睫。
1.缺乏意定监护合同的具体规定
《民法总则》第33条的规定确立了成年人意定监护的设定,其方式表现为书面,意定监护合同是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设立的中心内容所在,但仔细分析《民法总则》的规定,笔者认为其关于意定监护合同的规定仍有几个方面存有疑虑亟待进一步明确:
(1)“书面协议”的性质亟须明示。“合同的分类有助于合同法的妥当适用”,在平时较为多见的合同事宜中,根据其典型合同的规范,合同双方的权利以及义务需要及时被确定下来,民法的相关规定都可以作为其参考和依据;而不常见的合同类型则可根据其内容的特殊性从典型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找到落脚点。但是我国目前暂时还没有设置相对应的类型,意定监护合同的性质确定是迫切需要明示的内容。
(2)监护人范围的确定欠缺现实需求的支撑。《民法总则》第33条对监护人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表述为“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我国的监护制度有一项立法的创新,即除了近亲属以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其他人也可以成为监护人,这在亲属法领域突破了血缘的限制。弹性太强的规定会对该制度的具体适用造成一定的阻碍,究其原因体现在,第一,将“近亲属”纳入监护人主体范围实际意义并不太大,具体适用到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中,成年人的许多近亲属通常情况下大部分都会因为身体原因而导致无法完全实施监护行为,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近亲属的实际适用范围其实只是限定在了“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当中,对于父母而言,子女更多的是履行法定赡养义务,在出现问题时进而履行法定监护的义务,这样的话,法定和意定的监护可能出现交叉的状况;第二,“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组织或个人”对监护条件的规定太过宽泛,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进入监护的范畴之内,只要其有成为监护人的强烈愿望即可,意定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会对被监护人造成明显影响,法律需要对意定监护人的各项条件作出明确的规定,且需要严格并兼具可操作性,但是新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对于笔者提出的这些疑问和担忧似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很难让人找到可以信服的依据。
(3)意定监护制度生效时间的设定不具备完全的可操作性。《民法总则》第33条规定,意定监护人开始执行其监护事务应当是被监护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时。书面合同是意定监护人执行约定监护事务的凭证,在其生效后,监护人才开始履行其职责。首先,人缺乏完全的行为能力时,意定监护合同才会发挥作用,但是岁月的流逝毫无疑问会导致人类各项能力以及身体机能的衰退和退化,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担忧的问题,且衰退会是一个以螺旋式下降的漫长进程,人们往往很难准确地判断和把握被监护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的时间节点,更何况其认识能力很可能会出现反复等情况,若遇到此种情况,要准确判断出被监护人何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则也是非常困难;其次,在现实社会中,有一类人已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又没有完全失去行为能力,这类成年人依然同未成年人或者老年人一样需要被人照料,且不是短期就能结束的,但是制度把这类人排除在外,而此类成年人往往是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主要包含的对象,制度没有将这类人包括在内,显然会降低该制度应有的社会作用,同时也背离了该制度创建时的目的;最后,《民法总则》对于“书面合同”的效力、内容等相关维度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生效合同的重要内容包括权利义务、时间、违约责任、争议条款等,如果以上内容没有完全具备,即使合同成立,仍然不能避免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难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