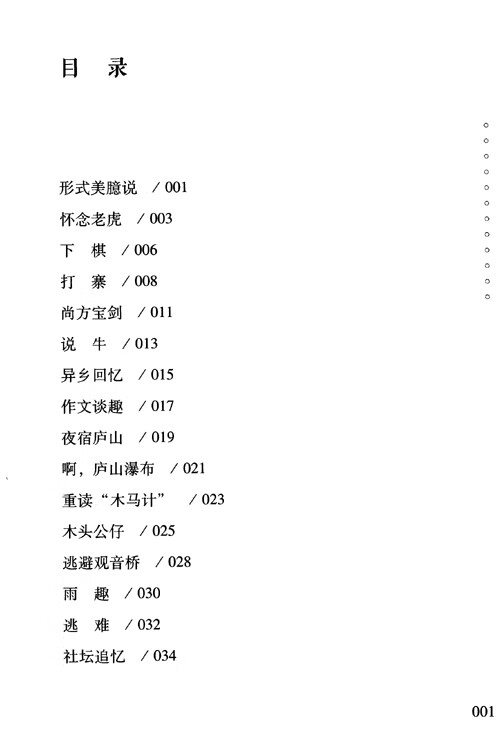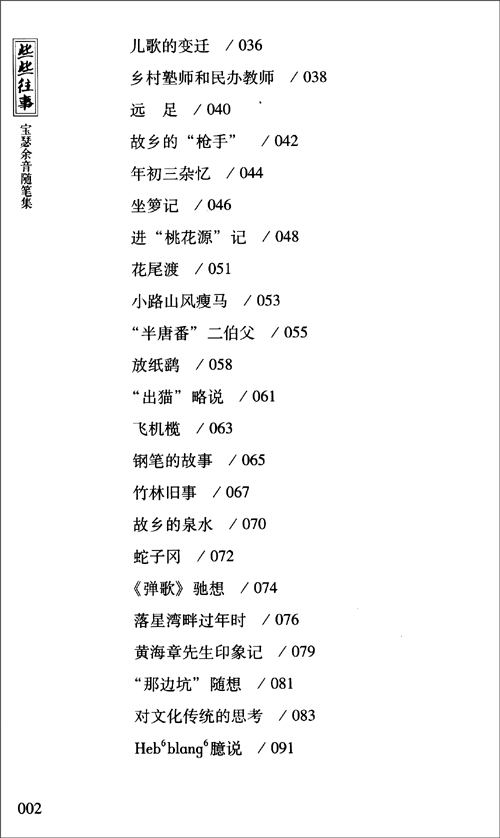《些些往事:宝瑟余音随笔集/创艺丛书·第七辑》:
每逢星期天,我窗下的内街就有小孩子群聚嬉戏,但从未听到他们唱过儿歌。想来也是,现在大人们经常可以“卡拉OK”一番,而可供孩子们唱的儿歌则太少了。
我的童年是唱着儿歌长大的。“麻雀仔,叼树枝,叼上冈头望阿姨。阿姨梳只崩沙蝴蝶髻,摘朵红花伴髻围……”多么优美!“鸡公仔,尾婆娑,三岁孩儿学唱歌。唔使爹娘教导我,自己精乖无奈何。”又多么天真烂漫!一班小朋友坐在一起,可唱“排排坐,食果果……”结队出门,便唱“龙舟舟,出街游……”假如在月下,唱“月光光,照地堂……”就更合适了,那一呼百应的场景,清脆而热烈得直薄云霄的童声,常常使大人们中止了谈话,个个绽出笑容来。
儿歌构成的文化熏陶,往往渗透着极可贵的因素。记得抗战时唱的《月光光》,末尾的词句是:“船沉底,浸死啪日本仔。一个浮头,一个沉底,你话好睇唔好睇!”很有时代感。而在我们的前辈,他们诅咒的则是“浸死啪红毛番鬼仔”。想来,这儿歌当作于鸦片战争后,透过它可见当时民众对帝国主义者的痛恨情绪如何感染着下一代。
鸦片战争后,“红毛番鬼”还派来了大批传教士。平心而论,传教士中也确有怀济世之心的好人,但就整体来说,传教本身却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手段。有侵略就有反侵略的呼声,这呼声也由孩子们承接了,于是有儿歌唱道:“磨利刀,杀耶稣,杀死耶稣有鬼做!”唱词粗俗,绝对不会是凭儿歌创作获奖的文人的手笔,只在粗俗中直喷出高昂的反帝情绪。1944年,我在逃难途中暂住一小镇,长日无聊,一群小朋友到处乱钻,钻进一座教堂。牧师当即向我们分发宣传品,请我们去听他布道。我们一哄而走,出了门,有人带头唱:“磨利刀。”其他人便放尽喉咙大唱:“杀耶稣,杀死耶稣有鬼做!”读者诸君,你们此刻在平心静气地阅读会觉得我们可笑吧:该杀的是日本兵,怎么又闹着去杀耶稣呢?怎么又对牧师喊打喊杀呢?今天确实太幸福了!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军队,这几十年,跟超级大国也过过三两招,并没吃亏。这个军队给诸君提供了平心静气区别对待外人的资本,而半个世纪前的中国,还是块被外人宰割的砧板肉啊!原谅我们吧,朋友!
随着战争的胜利,儿歌也变了。抗日战争胜利没几年,《月光光》的结尾就被唱成:“浸死啪红毛番鬼仔,一个浮头,一个沉底,一个匿埋门扇底,偷钱去买油炸鬼。”变得油腔滑调了。再后来,兴起唱“肥佬个头,大过五层楼”,越发离谱。更后,则小孩一律唱大人歌,儿歌几乎被扑灭了。现在,一些热心人重新推广《落雨大》等儿歌,.录成的盒带唱得颇优美,可惜影响似乎并不大,我就从未听到窗下的小朋友们唱过。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