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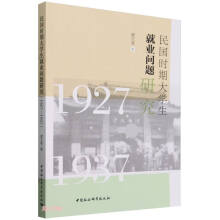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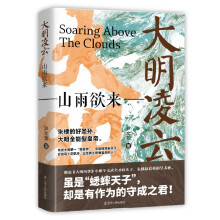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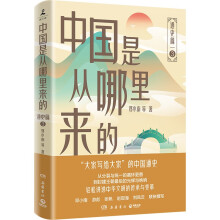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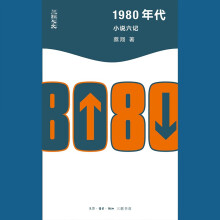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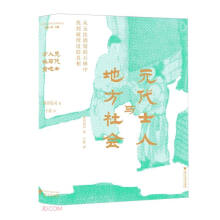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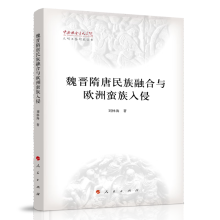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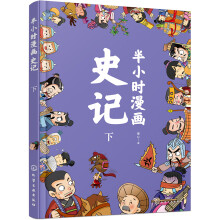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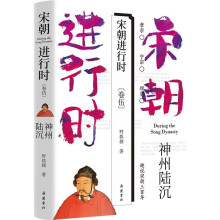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学术著作,皆漫画式地将衙门吏役普遍描述为贪腐成性、一心只为追求自身私利之辈,认为这些“为官之爪牙”的小人物在侵蚀着帝国统治的根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展示了与上述刻板形象大为不同的另一幅历史图景。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创制出了并奉行着一些非常精细的惯例、规矩与程序,但这些事实上发挥着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惯例、规则与程序,却不被清代的正式法律所承认,其中一些做法甚至历来被朝廷视为非法并下令禁止。不过即便如此,上述这些惯例、规矩与程序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在弥补着由于缺乏正式规则所造成的空隙。
本书超越那些将衙门吏役简单视为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描述,它不仅在瞿同祖等前辈们所做的先行研究之基础上做出了创新性的学术推进,而且揭示了迥异于马克斯·韦伯所描画的现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的另一种行政行为模式。
书吏和差役,帝国之“爪牙”,基层社会运行和帝国统治不可或缺之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刻画了清代巴县衙门的差役和书吏们生动形象。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作者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探讨吏役在维系帝国统治与基层社会运行中的“合理性”(不可或缺性),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些人物在清代县衙当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并思考其活动是如何可能影响到清代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
在构建以“爪牙”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中,作者表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术样貌,对我们深入理解官僚制、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话语分析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皆富有学术启发性。
清代地方衙门吏役的“腐败”
在传统认知里,清代地方衙门吏役常以“恶棍”的形象示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编制外的非正式人员,却避开官府对他们的管束,利用权力肆意敲诈勒索当地百姓。但作者颠覆了这一认识,他以巴县档案资料为依据,既探讨了清代地方衙门吏役一系列行为的“非正当性”,也研究了其“合理性”。——编者按
在我们关于中国帝制晚期县级行政的所有印象当中,流传最广且历久不衰的便是认为地方衙门吏役普遍贪腐成性。地方衙门的吏役们据说都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肆意敲诈勒索当地百姓,同时又能够避开官府各种旨在对他们加以管束的措施,而这使得这些邪恶的书吏与差役们成为人们在地方政府之施政舞台上经常遭遇到的恶棍。但是,此种印象主要源自精英与官方编纂的著述中所提供的那些历史证言。直到非常晚近,我们都还无法获得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超越此类单一维度的人物形象刻画。不过随着诸如巴县档案之类的清代地方衙门档案逐渐开放供研究者们利用,我们终于可以针对人们长期以来所抱持的某些假定进行修正。
首先,我们显然需要将历史上关于地方衙门吏役贪腐行为的表述,与地方衙门内部由各种日常做法与惯例性程序所构成的现实区分开来。如同我们在本书前面几章当中已经看到的,那套关于腐败与行政伦理的话语,经常被不同的当事人策略性地利用来达到各种特定的目的。例如,巴县知县们频繁地对这套话语加以利用,以作为警告吏役们切勿贪得无厌和督促吏役们遵照其所下命令行事的一种行政手段,而地方士绅们则使用与此相类似的策略,来强调他们自己在各种社区事务处理中所具有的那种权威在道德上和社会253上皆被人们认可。不仅如此,我们也已经看到,地方衙门吏役们自身也会经常利用此类修辞,来将他们当中的贪腐之辈与正直之人区分开来。
地方衙门吏役们对这些话语形构的运用,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他们所做的此种运用强调,应当将各种严格来说并不合法却属于惯例的做法,与那些甚至连各种非正式的行政行为规范也违反了的做法区分开来。而在绝大多数精英和官员们的笔下,这种区分即便没有被全然抹杀,也是变得模糊不清。但这种区分对任何试图超越那套关于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修辞,进而达到一种对于吏役们实际做法的有效理解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区分也表明,关于腐败的表述并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可以被创造性地加以改造与选用,以满足不同的个体在各种特定情形当中的需要。
首先从吏役们在地方衙门当中的存在本身来看,有时他们当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各种违反官方法令规定的行为,因此可以被定性为腐败。但是,这些行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于正式行政制度的缺陷而不得不然,故而它们尽管表现为一种腐败的形式,却是一种内生于正式行政制度本身之中的腐败,若无这些行为,则清代的各个地方政府将无法运转。因此,那种从法律角度严格加以界定的腐败标准,无法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清代地方衙门的吏役们许多从法律角度来看属于非法的行为之惯例性特征与功能性价值。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再次回到经常被认为是吏役贪腐之渊薮的某些行为上来进行观察,亦即各种规费的收取。在精英和官员们认为构成腐败的各种行为当中,没有其他哪种行为遭到的口诛笔伐,会比吏役们向到当地县衙打官司的民众收取案费的做法所受到的抨击更加众口一词或言辞激烈。实际上,衙门吏役向当地民众收取规费的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其他腐败形式的根源,无论后者是具体表现为超过朝廷规定的经制吏役额数招募了大量的编外人手,还是那些非经制吏役久踞其位而不从县衙告退。相较于吏役们其他任何做法,他们在承办案件过程中向当地民众收取案费之举,更是被描述为一种违反清帝国政府所奉行的那些道德伦理准则的行为,因为此种做法被认为导致个人私利侵入了公共事务的领域当中。清代雍正朝创设的“养廉银”制度,正是朝廷为了在其正式任命的那些官员当中防止此类将个人私利侵入公共事务领域之做法而出台的措施。清廷对于个人私利侵入公共事务领域进而导致腐败的担忧,也反映在《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当中针对“公罪”与“私罪”所做的区分上面,其中前者是指官员在执行官方职责的过程中犯下的那些虽属渎职、但并非为了从中谋取私利的行为,而后者则指官员完全出于假公济私、谋取私利之动机而犯下的违法行为。根据潜藏在不同行为背后的不同动机,官员们的渎职行为要么被归为公罪,要么被归为私罪,而那些被归为私罪的违法行为所受到的惩罚,将比犯公罪者更加严厉。
但是,鉴于清廷在法律上所规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存在着各种缺陷,通过非正式方式收取的规费便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行政运作经费来源。在地方层面,某些形式的规费收取及数额被认为构成了腐败,甚至连吏役们本身也对其予以禁止,但是也有其他一些收取规费的行为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被视作县衙司法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到了19世纪中叶,收取各种案费的做法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吏役们被允许收取的案费种类及数额有时还被刻在石碑之上,以供打官司的民众参考。而当衙门吏役们宣称其所从事的这份营生具有正当性及他们自己也有个人荣誉感时,这些人所诉诸的正是上述那一层面的做法。
与清代官员和精英们所言的不同,地方衙门的吏役们没有必要诱骗当地民众到县衙打官司,以期从那些不幸的受害者那里勒索钱财。那种认为地方衙门吏役收取案费的行为导致19世纪讼案增多的说法,长期以来令人感到困惑,因为从其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完全违反直觉。恰恰相反,吏役们向当地民众勒索各种案费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应当会阻止民众将细故纠纷告到知县那里,而不是像官员与精英们经常说的那样将会助长民众去县衙打官司。为了理解官员与精英们上述那种说法的背后逻辑,我们必须意识到,此说法乃是植根于一种认为普罗大众皆是被动行事并且彼此之间基本无甚区别的观念,而儒家关于道德型政府的理念也正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
根据孔子在《论语》中对道德型政府所做的经典阐述,在德政的氛围熏陶之下,平民百姓的行为将会更少为关于自身私利的算计所驱使,而是更多地受到当地官员及那些有教养的地方精英们的引导,就像风过之处草会弯腰那样。(译者注:原书此处系依据理雅各对《论语》之“颜渊”篇当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句的英文解说。)在此类正面的影响下,普通百姓(良民)就会自我约束,不将那些鸡毛蒜皮的纠纷告上公堂,而是通过调解这种社会性矫正制度来加以解决。事实上,地方民众将此类细故纠纷告到衙门的那种举动,只能被按照以下两种方式进行解释,亦即要么当地的官员与社区领袖们未能做到以其身体力行的道德教化来影响与引导民众,要么他们的此类影响与引导作用正在被那些为害地方且贪腐成性的衙门吏役与讼棍们所颠覆。
但是正如本书第六章所描述的那样,在晚清社会那种伴随着人口增长、社会分化与商业活动扩张性发展而不断加速的社会经济分化过程当中,地方上的民众完全有各种自己的充分理由到衙门打官司,而不是由于受到那些诡计多端的衙门吏役之诱骗才如此行事。而且,尽管当地的许多民众毫无疑问地会遭到衙门吏役需索案费的掠夺性行为之扰害,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地方衙门吏役收取案费的通常水平,要比清代官员与精英们笔下夸张描述的那些所收钱财数额少很多。清代官员与精英们针对吏役收取案费的行为加以夸张描述,其本身应当被视作一种试图以此来阻吓百姓不要再动辄到衙门打官司的努力。
虽然地方精英们所做的各种旨在对衙门吏役收取规费的行为加以约束的努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更根本的因素则在于地方衙门吏役们自身的各种生计利益。大部分的吏役并不是想通过敲诈勒索来让自己一夜暴富,而是想维持一种稳定的生活来源,以让自己能够过上像样的生活。在那些惯例所允许的限度之内,规费的收取被吏役们辩称说是必要、正当且公平的;只有超出这些限度而不合理地进行规费收取,而并非收取规费这种做法本身,才被吏役们认为构成了腐败。再一次地,那种通过在所准许的行为与不当的行为之间努力地重划界限而获得的非正式的正当性,既表现为案费收取数额之惯例性标准在地方上的成文化,又在知县们愿意就吏役们内部围绕待承办案件之分派而发生的各种争端进行裁决这一事实上得到了展示。
将那些允许吏役收取的案费种类及数额予以成文化,这种做法即便只是建立在某个非正式的基础之上,也会对当地百姓利用衙门公堂的方式造成影响。由于所收取的案费数额相对而言并非高不可攀,且收取的案费数额正在逐渐被加以标准化,于是县衙公堂便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一种不受民间调解过程中所积欠的那些人情债影响的纠纷解决手段。而且,到了19世纪,许多社区逐渐在经济上发生两极分化,而士绅领袖们传统上所拥有的那种权威也正在逐渐受到侵蚀,故而县衙公堂的相对公正,便使得它成为一个更受地方民众欢迎的纠纷解决场所。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建议说,应当将地方衙门吏役向当地民众收取案费的做法看作一种功能性或权宜性的腐败方式。考虑到并不是谁都可以随意出入清代的县衙公堂,不妨将收取案费的行为看作是为民众利用一种稀缺性资源提供了渠道。案费收取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则是,它为清代县衙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进而有助于为衙门的司法活动,以及其他政务事项提供财力支持。在上述这两层意义上,收取规费的做法乃是爱德华·范·罗伊(Edward van Roy)所说的“间隙性”(interstitial)制度的一个绝佳例证。所谓“间隙性制度”,是指从社会的各种间隙当中发展出来的、能够发挥其他方式都无法实现的各种功能的制度。按照爱德华·范·罗伊的说法,此类制度之所以被一些人认为在本质上属于腐败,256是因为在经济适应性组织行为与那些相对静止不变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差距,而在那些正经历着各种无处不在的变化的社会当中,经济适应性组织行为是被按照那些相对静止不变的价值观加以认知的。在他看来,通过凸显实践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裂,腐败行为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经济变迁的轨迹及那些后来出现的新规范加以识别。
虽然我赞同爱德华·范·罗伊将那些间隙性制度的成长视为反映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指数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存在着一个一元化的主流价值观体系(经济适应性组织行为这种新实践便被认为背离了此种主流价值观体系)的观点则有待商榷。就像所有关于腐败的定义那样,“功能性腐败”这一概念暗示存在着一种关于何谓非腐败行为的标准,并进而使得由特定人群就何谓腐败做出的一种特殊定义被优先加以考虑。因此,爱德华·范·罗伊的上述观点,不仅无法看到对非腐败行为这一假定规范的“腐败的”偏离是如何全面与普遍,以及遮蔽了那些具有规范性特征的不当行为与肆意妄为的不当做法之间的重要区别,而且还掩盖了那些关于腐败的表述本身是通过何种方式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
相较于那种通过对所谓“权宜性腐败(facilitative corruption)”与“堕落性腐败(corrupting corruption)”加以区分的方式来就腐败问题展开讨论的做法,另一种看起来更有帮助的学术处理方式是,将腐败一词本身及在实际历史情景当中被历史行动者们利用这一语词加以形容的那些行为进行相对化处理,进而重塑整个分析框架。尤其是,我们必须避免对任何规范加以优位对待,无论该规范是现下被我们自己所奉行的,还是在我们所观察的那个社会里面为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所拥有的。尽管本书所描述的那些非正式行政措施与被制定为法律的正式规范之间存在着距离,但前者并不能被简单视作一种偏离正式法律规定的形式加以分析。个中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在日常的实践领域,那些非正式的行政措施所构成的,并非对规范的一种偏离,而正是规范本身。我们与其追求对腐败下一个精确的分析性定义,还不如意识到正当行为与腐败行为之间的边界常常有着极强的渗透性,并且属于地方惯例而非官方法令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承认,腐败行为与正当行为之间的区别,经常被清代的人们在各种特定的情景与可利用的资源选项当中进行策略性利用。
然而,无论我们是否将清代地方衙门吏役们的那些朝廷法令没有规定的做法视作腐败行为,终究都不如审视此类做法与清代国家的正式行政架构之间存在的那道罅隙更为要紧。257作为一套非正式的办事程序,清代地方衙门吏役们的行事相对而言很少受到朝廷颁布的那些行政法的束缚,因此比正式制度更为灵活,进而能够更好地回应19世纪县级政府所承受的各种政务压力。例如,在19世纪上半叶,尽管清朝中央政府官员里面的改革派们不断强调执行政务者本身品性正直在施政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并主张节约地方行政开支,但各地县衙却不得不大量利用超出经制吏役额数招募进来的那些书吏和差役,以满足当时各种由于人口快速增长与人口结构分化而不断加重的政务需求。与此相类似的,规费的收取可以作为清代地方政府筹措行政运作经费的一种非正式手段,而且,这种做法并非诉诸直接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而是从当时正在发展的商业经济中分一杯羹。
并非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正式官僚机构在清帝国基层的存在感显然出了名的弱,但这套由各种非正式措施构成的制度,至少部分有助于清政府管理整个帝国。不过,如果说这套法外运行的行政制度通过某些方式有助于维系大清帝国的统治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是一套不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制度。正是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这套制度缺乏直接控制,才使得书吏和差役们首先将其在地方衙门当中的这份工作打造成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营生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儒家话语中的修辞使这种生计保持相对稳定。而且,吏役们在此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本身,反映出对非正式行政方式之依赖所造成的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后果,那就是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资源的垄断正在遭到侵蚀,无论是从物质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来讲皆是如此。相较于其他任何因素更明显的是,这种侵蚀使得地方社区的成员们能够获得这些资源,并进而利用它们对清帝国最底层的制度性装置与那些地方权力和权威之结构间的互动关系进行重新塑造。
第一章 非法的“官僚”们
第一节 学界以往的研究
第二节 19世纪的巴县
第二章 书吏
第一节 内部组织情况
第二节 人员类型
第三节 人数
第四节 出身背景与家庭经济状况
第五节 房规
第六节 非法行为的正当化
第三章 家人、朋党和派系
第一节 亲族关系
第二节 庇护人、派系与朋党
第三节 工房
第四节 结论
第四章 差役
第一节 内部组织与人员管理
第二节 服役期限、内部晋升与纠纷解决
第三节 “瞒上”
第四节 “岂尽无良?”
第五节 品行端正的公人与道德败坏的差役
第五章 不当的联盟与知县的手下
第一节 责任关系网
第二节 重思“爪牙”
第三节 社会基层的朋友们
第六章 司法的经济因素
第一节 案费与收入
第二节 焦点:围绕案件管辖分工与案费分配而发生的争执
第三节 控制与权威
第四节 余论
第七章 不可或缺之人的正当性
第一节 非正式的正当性
第二节 地方衙门吏役的“腐败”
第三节 权力网络
附录
附录一巴县衙门各房的差务分工
附录二巴县衙门书吏当中的金氏族人
附录三巴县衙门工房书吏们就互助及待承办案件分派所订立的合约(光绪二十年,1894)
附录四案费章程与三费章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
附录五巴县衙门各房案件管辖分工(光绪三十一年,1905)
附录六巴县衙门粮役就案件管辖分工订立的合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此书的一个耀眼亮点,是以“惯例”为分析工具,考察巴县衙门书吏和差役的人员构成,评估他们的人数与行为,推翻了以往那些印象式的夸张描述。特别是,基于廉洁奉公的高调职业伦理及维护这一伦理准则的律例规定,书吏和差役的定额薪资极低甚至一度被克扣殆尽,办公经费更是严重短缺,从而产生了名目繁多的规费。在清人看来,如果“规费”之外一钱不要,那么就不能算腐败。此书作者认为,吏役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腐败。律例对吏役的规制极为粗略,其所留下的空白,往往由“惯例”来填补。关于书吏和差役的利益分配、内部晋升诸问题,便是由惯例和合约来调整的。这一亮点的启示意义在于,若要理解清代中国的官场运作与民间秩序,则必须关注惯例。此书对吏役之“家族、朋党和派系”的分析,对“权力网络”概念的运用,亦有学术启发意义。
——徐忠明(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虽然中国学者自瞿同祖、缪全吉诸先生以来对明清时期的胥吏有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利用清代中晚期巴县档案为主要材料所做相同主题的研究,将这一群体置于具体的地方情境和日常行政运作的实况之中,使我们对其的认识更为深入。随着近年来清代县级档案的整理出版和各地大量地方文书的搜集与利用,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将会更为丰满、多样和细致。因此,此书无论在具体分析还是在理论讨论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家设官,以为民也。故凡官与民亲则治,与胥隶亲则否”(光绪《澎湖厅志稿》卷3“职官”),清官与好官必定要“严打”胥吏吗?针对这类指责书吏与差役的传统中国主流政治论述,《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运用详实的巴县档案,矫正了我们习见常闻的惯性思维,并就胥吏如何作为清代政治系统有效运作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借助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社会学理论视野,进行了极有学术意义的对话与发展。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典范之作,自其出版以来,一直广为学界称誉。该书着眼于清代地方治理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生态,生动且精准地描述了政府强权与社群自治的互动、交融乃至相互依赖,兼具实证厚度与理论深度。此外,在对县级档案的运用上,该书也是先驱者之一,引领了重大的方法论变革。如今它的中译版面世,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是又一次了解、剖析、学习“他山之石”的良机。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