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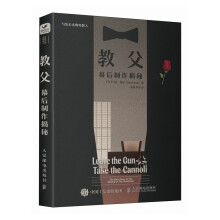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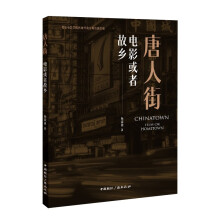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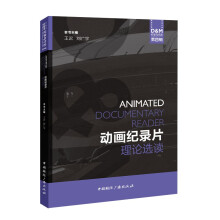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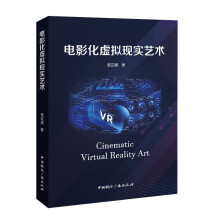

戈达尔:蒙太奇,我的美丽忧虑
本文节选自《电影手册》杂志1956年12月刊载的文章《蒙太奇,我的美丽忧虑》,是我采访的一位剪辑师阿涅斯·吉耶莫推荐收录的一篇文章。我们二人在聊天中提到戈达尔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导演是一个眼神,那么蒙太奇就是一次心跳”就出自此文。鉴于写下这句话时戈达尔还尚未拍出电影长片,它的简洁和洞察力着实令人惊讶。
……首先,蒙太奇是场面调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割裂两者要冒极大的风险。你不妨试试把节奏和旋律分开。影片《艾琳娜和她的男人们》和《阿卡丁先生》都是蒙太奇的典型代表,因为两者各自表现了一种场面调度模式。所以才会有制片人的那句至理名言:“我们留到剪辑室里再解决。”有效的剪辑能给一部影片带来的最大好处,恰恰就是给人一种它被导演过了的最初印象,否则就不会引起人的兴趣了。剪辑能还原那些被假内行和影迷所忽略的、短暂且富有魅力的现实,也可以将机遇转化为命运。普通大众会把剪辑手法与剧本设计混为一谈,还有比这更高程度的褒奖吗?
如果导演是一个眼神,那么蒙太奇就是一次心跳。两者的共同特点是预见:前者寻求在空间中预见,后者则寻求在时间中预见。假设你注意到街上一位令你倾心的年轻女孩,你犹豫了四分之一秒要不要跟着她,那么怎样才能传达这种犹豫?场面调度会把问题解读为:“我要如何接近她?”但是为了清楚表明另一个问题——“我会不会爱上她?”,你不得不赋予这四分之一秒以重要性,因为这短短一瞬间已经诞生了两个问题。因此,可能只有蒙太奇,而不是场面调度,方能既准确又清晰地体现一个念头的生命,或者说它在故事进程中的突然涌现。在什么时机呢?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在每一次情境需要时——在每一次一个镜头需要一种“惊奇效应”取代“阿拉贝斯克舞姿”时;在每一次场景转换之间,影片的内在连续性要求通过镜头转换将人物描写与情节描写重叠起来时。这个例子表明,谈论场面调度,就自动包含着蒙太奇。当蒙太奇效果在表达效率上超越场面调度时,后者的美感加倍,在一种类似于在数学中使用未知数的操作中,场面调度未曾预见的秘密因蒙太奇的魅力揭开。
任何拜倒在蒙太奇吸引力之下的人,亦无法抵挡短镜头的诱惑。怎么发生的呢?把“眼神”当成这场游戏的关键。眼神的剪辑几乎就是蒙太奇的定义,它有至上的野心,又臣服于场面调度。实际上,它是通过摧毁空间的概念,从而支持时间的概念,激发出精神之下的灵魂、机巧诡计背后的激情,使心灵战胜智识。翻拍版《擒凶记》中著名的钹声段落就是最佳证明。仅仅是清楚要让一场戏持续多久,就已经称得上蒙太奇了,正如考虑如何转场是拍摄问题的一部分。一部导演得很出色的影片给人的印象只是一段段首尾相接起来,而一部剪辑精良的电影则让人感觉不到任何导演的痕迹。在摄影方面,考虑到主题的不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中的战争场面绝对不逊于《航海家》。换句话说,通过运动给人一种时间持续的印象,通过长镜头给人一种特写的印象,这都是场面调度的目的,这与蒙太奇的目的正相反。在Moviola剪辑机前的发明和即兴创作,与在片场上的一样多。将一段摄影机运动剪成四段,兴许比保留一个镜头效果更好。再回到我们之前的例子,必要的时候,交换眼神只有通过剪辑才能表达得足够有力……
……因此,蒙太奇既否定了场面调度,又为它铺平了道路:两者是相依相存的。去导演意味着去计划,而关于一个计划的说法就是它被安排得好或坏。
这也是为什么说一位导演应该密切监督自己作品的剪辑,同理,剪辑师也要暂别胶水和赛璐珞,去片场感受一下弧光灯的热度。在片场走动时,剪辑师会发现一场戏有趣的地方究竟在哪里,明白这场戏哪里突出、哪里薄弱,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切换镜头,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只满足于简单地依据动作剪辑——那种最基础的蒙太奇。我承认,假如剪辑师可以不太机械地应用这种手法,倒也无可厚非,千万别像玛格丽特·雷诺阿那样:总是一个场景刚要开始变得有趣,画面就切换了。这样一来,剪辑师就是在迈出导演的第一步了。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时间的轨迹
与苏联电影经典时期发展起来的理论相反,塔可夫斯基并不认为电影的意义是由剪辑或蒙太奇创造的。于他而言,更重要的是剪辑必须挖掘出已拍素材中隐藏的意义。这不是说剪辑于他而言不重要,相反,他认为剪辑是整体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诚如下文所言。
一部电影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只有电影整体才是艺术作品。我们只可能相当主观地谈论它的组成元素,为了进行理论探讨而人为将其拆解为各种元素。我同样无法接受“蒙太奇是一部电影的主要构成元素”的论断,这是“蒙太奇电影”论的主将们继库里肖夫和爱森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仍在坚持的理论,这么说就好像一部电影是在剪辑台上拍出来的。有人曾多次中肯地指出,每种艺术形式都涉及“剪辑”,从选择和整合这层意义来说确实如此,都需要对部分和片段进行调整。电影画面产生于拍摄期间,并存在于景框之内。因此在拍摄过程中,我会专注于景框内时间的轨迹—为了再现它、记录它。剪辑连接起已经填满了时间的镜头,组成影片完整而鲜活的机体;而在影片的血管中脉动、流淌并为其注入生命的时间,则如同有着变幻节奏的血压。
所谓“蒙太奇电影”,即利用剪辑组合起两个概念,从而产生一个新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似乎有悖电影的本质。艺术永远不能以概念的你来我往为终极目标。形象是与实体和物质结合在一起的,却可以沿着神秘的途径抵达超越精神的领域——也许这就是普希金说“诗歌必有些许蠢钝之处”所要表达的意思。电影诗学是对象征主义的抵抗,是我们日常涉足的最基本的物质的混合。从导演对事物的选择和记录来看,一帧画面就足以表明他有没有才华,以及是否具有电影化视觉的天分。
归根结底,剪辑最终只不过是镜头排列的一种理想方案,而这种理想方案已经事先存在于所拍摄的素材之中。
……
回顾我自身的经验,我必须要说,剪辑《镜子》的工作量十分庞大,涉及近20种甚至更多的剪辑方案,不光是一些镜头顺序上的改变,而且关乎结构及段落顺序的重大变化。有好几次似乎根本无从下手,这可能意味着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不可接受的失误。电影无法自成一体,它没有统一性,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也没有逻辑,好比是一盘散沙。后来某个晴朗的日子,不知怎地,我们设法想出了一种不抱希望的重组方案—这部电影诞生了,素材“活”了过来。电影的各部分开始相互作用,似有血脉相连。当这孤注一掷的尝试成果被投射在银幕上时,一部电影在我们面前诞生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相信这个奇迹—这部电影保持了完整性。
……
《镜子》有约200个镜头,这对一部这么长的电影来说非常少,通常同样长度的影片有约500个镜头。这部影片镜头之所以少是因为镜头持续时间很长。
尽管镜头的组接决定了电影的结构,但它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会创造节奏。
是镜头中流动着的独特的时间,创造了电影的节奏。节奏不是由剪辑片段的长度决定的,而是由在其中流动着的时间的挤压决定的。剪辑无法决定节奏,在这方面,它只能作为一种风格存在。实际上,无论剪辑与否,时间都会随影片流逝,时间流逝不因剪辑而发生。画面中被记录下来的时间轨迹,是导演在剪辑时必须捕捉的东西。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