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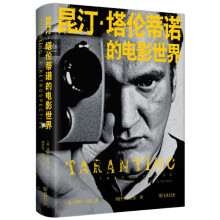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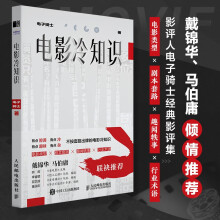




欧文·辛格的父母从奥匈帝国移民美国后在科尼岛开了家杂货铺。电影也是杂货铺,也是游乐场。辛格的《电影哲学:爱与神话》妙用艺格敷词,让我们看到种种神话原型的电影变体,将复数的爱的多元、暧昧、无解以及蕴于其中创造性充分展演。用心的读者会发现,他重现了电影角色上升或下降的场面调度,营造出本书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即人类的沉沦与超越。当然了,这部书也是一份与众不同的迷影片单。辛格曾说:“生命的意义......不是早就在那等着我们发现的东西......我们寻找的其实是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的创造模式。”理解神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无论如何,我们仍要爱电影,爱人,爱这个世界
【1】看电影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做梦。在看电影/做梦时,我们会沉浸在被亵渎地暴露在眼前的事物中。有时,我们会对梦境产生消极的反应,抗拒某个不断出现的“不速之客”。我们甚至会强迫自己醒过来,就像走出剧场的观众。不过,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屈从于自己被动的状态,就像意识停摆的观众接受甚至享受做梦时拂面而来的轻松与不羁的愉悦。当在私密的环境中观赏仅为你我放映的电影时,我们真像是望着自己梦境的茫然的观众。
在某种程度上,梦里存在着我在自己关于爱的理论中称之为“赠予”的东西。我们在梦中受惠于某种免费表演。这种免费表演通常是视觉的,也可能是听觉的。我们让它裹挟着自己,感到惬意——就像我们清醒时在最富有创造性的状态下感受到的惬意。梦比我们清醒时感知到的世界的碎片混乱得多。大脑不睡觉。它赋予这样的情境某种意义,弥合充斥在绝大部分梦境中的混沌。因此,我们欢迎梦的造访,尽管事后回想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时可能会感到不适。
不论电影中是否存在明确的神话表达,总的来说,它们重现了做梦的上述特征。电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原因在于技术能够融合两种实践:书写神话,以及在有意识的经验中生动地模拟人们每天睡觉做梦时发生之事。这也才经历了一百多年。
【2】在奥维德(Ovid)讲述的皮格马利翁神话中,我们得不到多少有关伽拉忒亚(Galatea)的信息。她是皮格马利翁创作的雕像,后被维纳斯赋予生命。我们在《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中读到,伽拉忒亚一有意识,“就眨眨眼,泛红了脸,盯着他。她的创造者,她的爱人,她的男人。在他身后,天空明亮。为此,她感谢他,感谢女神”。一对恋人即刻成亲。在维纳斯的安排下,一个孩子诞生了,叫帕福斯(Paphos)。这个名字后来成了地名。这个地方是献给维纳斯的。奥维德没再说其他关于伽拉忒亚的事,也没说皮格马利翁对她的爱意味着什么。即便没有这些信息,故事的神话功能也已经完成了。
由安东尼·阿斯奎斯(Anthony Asquith)、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导演,盖布里埃尔·帕斯卡(Gabriel Pascal)制片的1938年版《卖花女》属于皮格马利翁神话的变体,与此相应,爱莉萨·杜立特(Eliza Doolittle)在电影里被呈现为既活在过去也活在当下的姑娘。她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由服饰风格和汽车年代即可看出,但她体现了一种“新女性”的吊诡。这种“新女性”出现在19世纪最后二十来年。当萧伯纳在1915年完成戏剧剧本,并在1938年完成电影剧本时,他借了这些吊诡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依然弥漫的东风。《窈窕淑女》的全球成功证明了这些吊诡在其他文化中也一直很重要。同《淑女伊芙》一样,《窈窕淑女》与《卖花女》探索了现代女性一个重要的维度。
【3】更能代表创造性艺术家的是米洛斯·福尔曼(Miklos Forman)的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1984)中的莫扎特。新婚的莫扎特夫妻贫困潦倒,岳母骂莫扎特是饭桶,违背了好好照顾她女儿的誓言。这个激动的女人怒形于色,声音高亢。莫扎特盯着她,竖着耳朵,一言不发。我们看了前面几场戏,对莫扎特很是同情:岳母盘算着把作曲家当作光鲜的婚姻战利品纳入囊中。莫扎特的生命故事深深吸引着我们,我们原本随着一个饱受婚姻不公的天
才的视角品尝世味,但很快发现,这在那场戏中微乎其微。这场戏没有被任何评论打断,而是变为充斥莫扎特脑海的作曲过程。他听着岳母撒泼,但那声音成了《魔笛》(The Magic Flute)中夜后咏叹调怀恨在心的花腔女高音。我们讶异、欢喜,这就是莫扎特默默屈就岳母时发生的事情。对婚姻问题的心理分析也许并不着调——事实上,这对于欣赏咏叹调的音乐内涵很重要,但莫扎特无疑将这些问题转化为创作素材,然后超越了它们。
前言
导论:神话与电影的哲学维度
第一章 《淑女伊芙》
第二章 皮格马利翁变体
第三章 《女继承人》与《华盛顿广场》
第四章 谷克多:以电影写就的神话诗歌
第五章 库布里克与费里尼的神话书写
注释
索引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