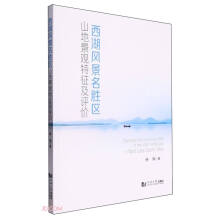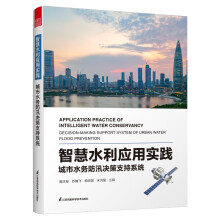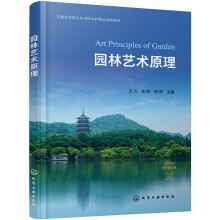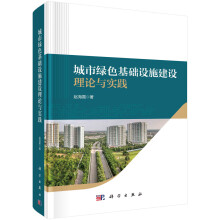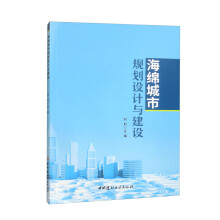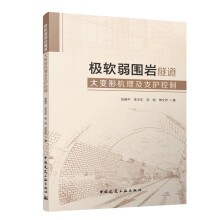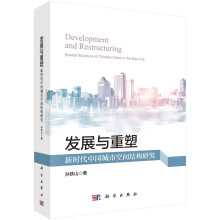第一章 绪论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走向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城市化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也成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2018年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5%,预计2050年将达到68%。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列为17个发展目标之一,国际生态城市研究也从追求生态效益扩展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欧盟自2010年评选“绿色之都”作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倡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将良好的城市环境、经济增长与优质生活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改变了城市地表热环境与水文循环过程,城市热岛、暴雨内涝、空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我国城市化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具活力和潜力地区的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问题集中且易激化的高度敏感地区(石忆邵,2014;方创琳,2014)。2015年12月,时隔37年后再次召开的全国城市会议明确提出了“城市发展安全第一,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的行动目标。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排部署在全国全面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简称“城市双修”)工作,以修复城市生态,改善生态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科学认知“城市病”的形成机制并提出符合国情背景的生态调控与治理措施是制定城市居住环境适应机制的先决条件。
城市生态空间是城市中除建筑、道路等功能性人工硬化表面以外的空间,包括城市绿地、湿地及立体绿化等,提供着污染物减排与控制、生态承载力提升和人居环境质量改善等重要功能,对于保障城市生态安全与实现生态文明目标至关重要。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及周边原有生态景观经常被生产生活空间吞噬占用。而在以往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生态空间也是作为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补充,绿色生态景观仅是在生产生活空间内见缝插针式地布局,未充分考虑发挥其生态环境功能所需的空间条件。因此,在城市空间有限的前提下,如何依靠科技进步,在生态空间组成、结构及格局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对提高城市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效益、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与保障生态安全有重要实践意义。
第一节 生态空间及其格局
19世纪初期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化加速并产生诸多城市问题。19世纪30年代英国大城市传染病流行,开辟绿色公共空间、提供健康运动场所受到关注。到50年代,欧美大力推动城市公园建设,如伦敦皇家公园、纽约中央公园(王甫园等,2017)。1898年Howard提出了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相结合的田园城市理论,完善生态基础设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空间体系成为20世纪城市建设的新主题。在我国城市生态空间概念的发展主要经历了5个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城市生态空间是以游憩功能为主的私家园林形态存在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8年),我国城市改造与规划学习苏联文化休闲公园模式,建设了许多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公园绿地,并提出完整的绿地系统概念;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园林工作会议召开,城市绿化法规与管理条例建立,推动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在20世纪90年代生态浪潮冲击下,我国城市建设开始注重将生态学与城市景观相结合,恢复城市自然特性,创建园林城市和山水城市。21世纪以来,城市化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引起关注,生态文明思想与理论成为新时代城市生态建设的主基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合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扩大城市生态空间”。因此,城市生态空间是随着城市化发展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而形成的新概念。
城市生态空间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中城市土壤、水体、动植物等自然因子的空间载体”(何梅等,2010),也是城市中绿色生产者与非生物环境构成的自然半自然地域空间(徐毅和彭震伟,2016)。王甫园等(2017)将城市生态空间界定为城市地表人工、半自然或自然的植被及水体等生态单元所占据的并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王如松等(2014)认为,城市生态空间是指城市生态系统结构所占据的物理空间、其代谢所依赖的区域腹地空间,以及其功能所涉及的多维关系空间,即包括生物栖息代谢的自然生态空间和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生态空间。王宝钧等(2009)认为,城市生态空间包括城市行政生态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两重含义,前者是指行政界线圈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后者是由自然过程决定的城市生态空间范围,后者往往大于前者。李荷和杨培峰(2014)认为城市自然生态空间是区域生态边界范围内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一定生态影响,促进城市呈现稳定状态、维持城市生态绩效和保证生态收益的空间环境总和,空间范畴包括城市内部人工自然生态空间和生态边界与城市建设边界之间的自然生态空间。综合以上概念,本书将城市生态空间界定为,城市中绿色植被及水域所占据的立体空间,是与构筑物和路面铺砌物覆盖的城市建设空间相对的空间,是维持城市空间平衡发展和提供生态服务的基础,也是人们游憩娱乐、观光休闲和城市形象感知的重要场所。
城市生态空间格局是城市生态要素的空间配置,是生态空间优化调控的先决条件。徐毅和彭震伟(2016)发现,1980~2010年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存在不平衡演化特征,包括生态空间的数量规模演化与结构特征演化,总体表现出上海城市外部生态空间缩减、内部生态空间增长与生态空间总量减损。目前城市生态空间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其中,“3S”技术和空间统计方法应用日益广泛和成熟,结合景观格局分析、土地利用和功能布局理论,出现一大批实证成果,揭示了不同城市生态空间格局现状和优化方向。例如,姚娜等(2015)基于“3S”技术与景观分析方法,识别出1992~2013年北京市平原区生态空间比例由53.20%下降到40.97%,三环附近景观破碎化严重。
第二节 生态服务功能评估
随着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凸显,城市规划研究者开始探索城市生态建设路径。20世纪60年代末,McHarg提出“设计遵从自然”的城市规划思想。1995年,Forman引入“斑块-廊道-基底”模式,提出了景观生态规划。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绿地生态网络规划”“绿色(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海绵城市”“城市通风廊道”等一系列基于自然的城市生态建设技术。随着生态系统服务(Costanza et al.,1997)理论的发展,城市生态系统的供给、调节、支持与文化功能等的维护与提升也越来越受到城市生态研究者的关注。在中国,俞孔坚(2009)提出从自然过程出发,开展城市安全格局构建及废弃地的生态恢复;张慧(2016)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了南京市生态安全、水生态安全、城市通风系统的综合安全格局。随着人类对城市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复杂性、自组织、抵抗力与恢复力等特征的认识渐趋全面,ICUN(2012)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旨在以高效利用资源和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挑战,同时提升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主要体现在将这种理念纳入政策制定的主流之中,包括水资源、粮食安全、农业、生物多样性、环境、灾害风险、城市居住地及气候变化等领域。NbS这一概念受到了欧洲规划专业人士和决策者的广泛认可。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辅助决策与规划者改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近年来,一些评估模型,如CITYgreen模型、i-tree模型、InVest模型及BUGS模型也被应用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评估。随着NbS的快速发展,对NbS实施的效果评估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例如,Raymond等(2017)结合全球10个城市的应用实例,建立整体框架,评估了跨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系统的NbS实施成本效益。而Panno等(2017)对米兰Parco Mord Milano公园实施NbS的生态社会文化效益进行了评估。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外城市就将生态学原理引入植物景观设计中。例如,Avissar(1996)研究发现,植被能显著影响城市区域的风、温度、湿度和降水,如果城市规划适当,生态空间可以抵消城市发展中人类活动产生的负面效应。到1999年,Bolund和Hunhammar(1999)初步阐述了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与分类,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奠定了基础。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全球城市化程度已达55%,2050年将上升至68%(United Nations,2018)。随着快速城市化的推进,全球城市建设区面积急剧扩张(Seto et al.,2012),原有生态空间大幅缩减(Shen et al.,2021),同时,城市生态服务功能明显降低(Su et al.,2012;Estoque and Murayama,2013)。Atif等(2018)分析了全球116篇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相关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生态服务研究相对较少。Cilliers和Siebert(2012)综述了非洲城市生态服务相关研究发现,非洲城市生态服务研究集中在德班和开普敦等少数城市,且对城市生态服务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
国内学者基于遥感影像数据与景观指数模型,开展了大量城市景观格局演变(Aguilera et al., 2011)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变化的研究(李锋等,2011)。徐毅和彭震伟(2016)发现,1980~2010年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存在不平衡演化特征,包括生态空间的数量规模演化与结构特征演化,总体表现出上海城市外部生态空间缩减、内部生态空间增长与生态空间总量减损。但是这些研究侧重景观格局指数的刻画或生态系统服务的简单经济价值换算,对景观格局演变影响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学机理重视不够。
城市生态空间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其中,“3S”技术和空间统计方法应用日益广泛和成熟,结合景观格局分析、土地利用和功能布局理论,出现了一大批实证成果,揭示了不同城市生态空间格局现状和优化方向。例如,姚娜等(2015)基于“3S”技术与景观分析方法,识别1992~2013年北京市平原区生态空间比例由53.20%下降到40.97%,三环附近景观破碎化严重。荣月静等(2016a)应用1985年、1995年、2005年、2015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基于Logistics-CA-Markov与InVest模型对南京市土地利用与生物多样性功能进行了评价,模拟预测了南京市2025年3种不同情景(自然增长情景、生态保护情景和土地优化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发展方向。
城市生态空间数量规模反映程度,对生态功能有直接影响。李锋等(2011)应用遥感信息技术与生态服务评估方法,分析认为常州市区1991~2006年生态服务价值的大幅减少是生态空间面积的大量下降所造成的。曾忠平和彭浩轩(2018)基于1988~2015年近30年多时相遥感影像,发现武汉市南湖地区湿地累计消减1563hm2,极大降低了区域渗水容水功能,内涝灾害风险明显增加。程琳等(2011)通过对中国9个超大城市1995年与2008年土地利用结构比较,发现中国超大城市整体生态系统服务均呈弱化趋势,原因主要是城市用地结构变化。陈爽等(2008)利用1986~2002年TM影像发现,虽然南京市生态空间面积总体平衡,但景观格局呈现破碎化与人工化趋势,导致生态空间服务功能下降,简单的面积控制难以减缓功能退化,需要多方面干预与调控行为。为此,保证一定规模的生态空间是保障生态功能的关键。张慧(2016)采用InVest模型-Biodiversity模块评估了南京市生物多样性在空间上受到威胁的程度,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