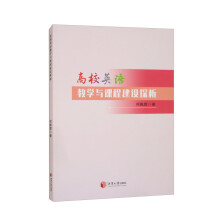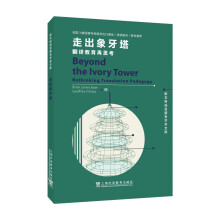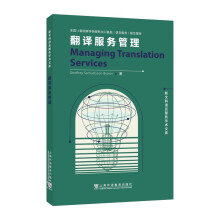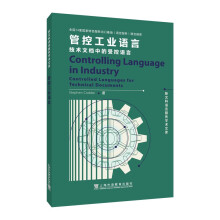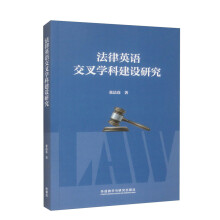第1章 绪 论
1.1 引 言
认知诗学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运用认知诗学的相关概念可以解释文学语篇中意义产生的动态过程。本书以英国当代作家戴维 洛奇的代表作《小世界》为语料,在对古典浪漫传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认知诗学角度出发,结合文学批评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原型”的研究,探究小说中浪漫传奇“原型”在读者头脑中产生意义的过程和审美效果。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和科学一直设法依据事物的本质认识并定义它们。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宣称依据事物属性(attributes)进行的定义都是基于偶然的发现,但这样的例子却数不胜数。原型范畴(prototype)这一概念是在人们探索事物本质和人类原初状态时产生的,原型范畴中的属性是根据巧合发现的事物特质。也就是说,人类*初探究认知世界的方法和知识是通过诸如各种偶然性和原型范畴化之类的方法获得的。本书写作的目的也是继续探究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事实上,人类从未停止找寻理解世界的方式。
阅读小说是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尽管小说中是虚拟化的现实社会,但小说提供给人们一个完全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崭新视角来理解事物。有些小说刻意与诸多文学作品产生联系,形成宏大的互文网络。这些互文网络经常以名称、意象、隐喻和典故等来体现其关联性,这无疑增加了读者在建构文本意义时的认知难度,但同时也增添了读者阅读的趣味性和挑战性。此类阅读犹如读者、作者和文本之间的文字游戏,《小世界》就属此类。
小说开篇,作者洛奇就引用小说家詹姆斯 乔伊斯(James Joyce)的话—“嘘!当心!一片回声之地!”—来提醒每位读者注意小说中所出现的不同声音。事实上,从小说题目中读者就会有所察觉,因为副标题中的“浪漫传奇”一词会提醒读者想到很多有关这一文类的相关知识。在看到题目后,读者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猜测,比如: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吗?这是一个有关中世纪骑士为荣誉或为圣杯而战的故事吗?还是说这是描写学者哪方面故事的小说?
毫无疑问,如果作家本人在浪漫传奇、文学批评、文学史方面没有广博的知识,那么他是不可能创作出这样一部作品的。据笔者统计,《小世界》共与其他48本小说产生了关联,并且,小说引用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中“四月是*残忍的季节”一句开篇。以一本小说为向导来接触并了解48本相关作品,这对于读者而言不仅是一次文学的冒险,也是一次如何使故事生成意义的挑战。小说含义在诸多文学作品之间的“穿越”中得到深化,而能够成功构建小说意义是欣赏其艺术及审美价值的关键。
对于读者而言,建构《小世界》文本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双重解码”过程,也就是说,作者在写作中同时使用互文反讽和隐含元叙述这两种技巧。这一概念是建筑学家查尔斯 詹克斯(Charles Jencks)首次提出的,对于詹克斯而言,后现代主义建筑“至少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表达自身”(Jencks 2002:32) :一方面,对于少数建筑家而言,他们更关心具体建筑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则关注建筑展示给大众或当地居民的意义。詹克斯进一步定义说:“后现代主义建筑或艺术作品是以少数精英为对象的,偶尔也会面对大众。针对前者,它使用了‘高层次’编码,对于后者,它使用了大众解码。”(Jencks 2002:36)可以看出,一部好的作品是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需要的作品。针对大众读者,文学可以作为一种消遣娱乐;而对于那些知识渊博的读者而言,在阅读过程中他们已经与作者达成了某种默契,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他们穿梭于不同作品之间,再结合文本本身,建构甚至重构作品的深层含义。因此,双重解码不是贵族化的噱头,它是作者表达对读者智慧和善意的一种尊重。
许多人的传统观点是,理解精心布局而又情节复杂的长篇文学作品是一个自然的、看似自动的认知过程。然而,认知诗学研究表明,即使是*短小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也需要相当复杂的语言和认知操作。此外,“无论是语言还是心理过程(或两者兼而有之),人类为了相互理解,对不同的概念结构都进行了命名,如脚本(scripts)、图式(schemata)、心理和认知模型(mental and cognitive models)、框架(frames)、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和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s),以及世界理论(worlds theories)”(Gavins 2007:3)。文学作品可被看作一种认知的产物,是人类用来帮助、增强或改善认知的方式之一。从认知角度来说,它们可以被当作一种基本的认知禀赋来探究。莱斯利 杰弗里斯(Lesley Jeffries)提出文学理解所需要的是“一种意义模型,它的两级是人类对文本*共通的一般理解和基于个人经验的*个性化的理解”(Jeffries 2001:341)。意义生成过程是认知诗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因此,伴随着20世纪认知科学的发展,认知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处于发展中的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涉及运用认知语言学、心理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分析和阐释文学文本,并依此进行批判性实践。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认知诗学与读者反应批评和文体学密切相关,有着深厚的语言学基础。因此,认知诗学适合于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致的语言分析,它强调语境在意义创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关注读者如何处理文本语言,所以它与认知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应用于语篇分析的成熟理论有指示语理论、语篇世界理论、图式理论、脚本理论及其在语篇意义理解中的作用。
1.2 戴维 洛奇简介
小说家约翰 福尔斯(John Fowles)曾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成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转引自Onega 1989:59)他认为批评家的知识在不知不觉中会操纵小说家的创作。然而,福尔斯的文学批评意识和其他诸多此类著名双栖人物的出现,表明这两种职业是可以完全兼容的。此外,福尔斯本人也承认英国文坛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马尔科姆 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另一个则是戴维 洛奇。
戴维 洛奇,1935年生于伦敦,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洛奇1967年获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1960年至1987年在伯明翰大学英语系任教。1987年,他提前退休,专心从事写作。他是伯明翰大学现代英国文学荣誉教授、英国皇家文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会员,并以其突出的文学贡献获得大不列颠帝国勋章和法国文艺骑士勋章。截至2019年11月,洛奇共出版了14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和一些短篇故事、15部文学批评作品。他先后获得了十项大奖,如白面包奖,并多次入围英国布克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7种语言,他的小说主题主要是自我发现之旅。
洛奇的小说被贴上了许多不同的标签,而其中*引人注目的当属“学院派小说”。当洛奇的小说出版后,特别是在《好工作》(Nice Work 1988)出版后,评论家们称《换位》(Changing Places 1975)、《小世界》(1984)和《好工作》为“校园三部曲”。也有人认为洛奇的小说是“问题小说” (Lodge 1971:22),还有人因为其创作的内容中包含天主教因素将其归为“天主教作家”。诸如此类的标签还有“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等等,从中可见其小说在创作内容、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多变性。除了创作小说之外,洛奇还出版了很多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籍,如《十字路口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 1971)、《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 1992)等。这些标签和诸多文学评论著作一方面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激起读者极大的好奇心,大家情不自禁想要去探索为何洛奇的小说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论,以及小说与理论之间的联系等。
事实上,这些标签都适合描述洛奇的小说,但都只涵盖了小说的部分特征。洛奇的“校园三部曲”主要讲述教授们的校园生活。由于其小说具有非常吸引人的情节和浪漫的人物,因此深受读者喜爱,并因此被冠以“流行小说家”的称号。而“问题小说”的叫法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非是从文学角度出发进行的命名。“问题小说”主要是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社会冲突方面的文学作品。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书中,洛奇探讨了英国小说家在现代主义和实验主义兴起后,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面临的困境。这关系到不同小说家所选择的写作风格及其写作取向。此阶段的小说家在尝试不同的风格和主题,因而被冠以不同的称谓也是在情理之中。
1.2.1 戴维 洛奇作品的文体特点
作为英语文学教授,洛奇在文学史、文学作品阅读和文学理论方面的广博、深入和全面都无须赘述;作为作家,他自觉而巧妙地将不同文学思想融为自成一派的文学创作理念,借用不同写作技巧—如讽刺、文学典故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他的小说是知识、智慧、技巧和实验的结晶,正如洛奇所说:“我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小说家。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对自己文本的要求与我批评其他小说家文本的要求是完全相同的。”(王菊丽 2005:2)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
洛奇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运用了不同的叙事和语言技巧。他的小说主题相对稳定,但是风格多样。自出版小说《大英博物馆的倒塌》(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1965)开始,他就逐渐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主题、技巧和兴趣。之后,他创作的所有小说都把大学生活和天主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洛奇的小说风格多样,独具特色。洛奇说:“我不是用一种风格在写作,而是用多种风格在写作,因为不同风格不仅代表着不同兴趣和想法之间的冲突,有时候不同风格本身存在的冲突更加突出。”(罗贻荣2010:2)从中也可以看出,相较于其他作家,洛奇对语言的看重绝非一般。
洛奇对小说语言的特别关注使其有别于其他作家。在《小说的语言:英语小说批评与语言分析论文集》(The Language of Fiction: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Verbal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Novel)一书中,他写道:“小说家的媒介是语言,无论他做什么,作为小说家,他都是在语言中和通过语言来做的。”(Lodge 1966:xiii)此外,洛奇还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对形式主义批评比对意识形态批评更感兴趣”(Lodge 1981:x),从其文学批评著作《小说的语言》到《巴赫金之后:小说与批评论文集》(After Bakhtin: Essays on Fiction and Criticism 1990)来看,他的所有批评都可归为形式主义批评范畴。这些书更注重对文学形式、体系、结构等问题的探索,将审美形式和技巧置于比小说内容更重要的位置。布拉德伯里和其他评论家对洛奇的评价是:作为一个批评家,洛奇更偏爱语言分析而非人文价值,偏爱“魔鬼的形式”而非“忏悔的倾诉”(R. A. Morace & R. Morace 1989:130),这类似于伯纳德 伯贡齐(Bernard Bergonzi)的说法:“作为小说家,洛奇的责任感之核心是对形式的关注,以及他作为评论家的兴趣。”(Bergonzi 1995:59)
在过去的40年里,洛奇一直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小说诗学。洛奇运用新批评的方法,企图寻求以语言为中心的、能够像解读和评价抒情诗一样的、可有效运用于小说的批评方法。然而,洛奇在《小说的语言》(2015)第二版的“后记”中承认,这一努力并没有完全成功。虽然对小说的解读和评价不能完全依靠语言,但语言的自觉性对于小说家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理论时期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拉康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应用语言学等都对洛奇的写作方式产生了影响。他阅读了罗曼 雅各布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