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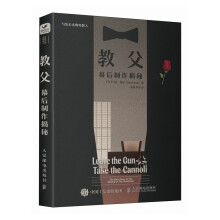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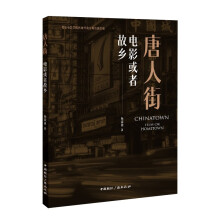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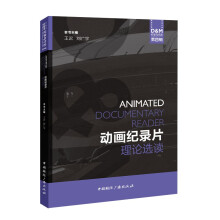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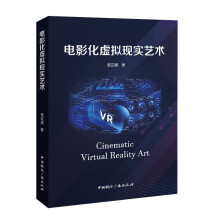

* 本书是“北京电影学院学者文库”系列的一种,本系列图书汇集了北京电影学院具有影响力的一批知名学者的优秀科研成果和从业经验总结。不仅是对北京电影学院自身教学、研究等经验的梳理,也从一个侧面为中国特色的电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做出独特、全面而重要的贡献。
* 谢飞,“第四代”导演的代表,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和金熊奖、获得1995年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艺术贡献奖;知名学者、教授,获得国际影视院校联合会(CILECT)杰出教师奖、平遥国际电影展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本书收录了谢飞教授从教50余年来在影视创作、电影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不只有其代表作的导演阐述还有其对父母、朋友的回忆文章,内容详实、语言真挚,对电影学院的学生以及喜欢、热爱电影的人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借鉴意义。
与谢飞谈电影
杨远婴:在您已知天命的时候做访谈,您更愿意从哪里开始呢?是创作,还是人生?
谢飞:当然是创作,人生还在继续呢。虽然已经跨了世纪,但中国的历史目前还不能做出定论,个人的情况也一样,还在发展变化呢!
杨远婴:那您就描述一下您的创作吧!
谢飞:我的创作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始,到现在共拍摄九部影片,其中有三部并不经常提起,即 1977年、1978年拍摄的《火娃》《向导》和 90年代初期拍摄的《世界屋脊的太阳》。拍《火娃》《向导》时“四人帮”刚刚倒台,大家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但学了那么多年的导演专业,总想争取一个实践和创作的权力,于是就急急忙忙搞了这样两个东西,现在看来完全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我在教学和艺术总结中一般不提它们,因为它们的内容和方式与我个人的艺术理想没有什么关系。1991年拍摄的《世界屋脊的太阳》是一部概念化的宣传片,但当时为了得到去西藏看看的机会,就拍了这个电影。这三部影片都可以说是旧的传声筒式的作品。《火娃》和《向导》之后,我开始认真反思,感到创作必须有感而发,电影应该艺术地表达个人对人生、历史、社会的看法。
杨远婴:您如何为在此之外的六部影片定位?
谢飞:我把它们叫作文化艺术片。电影一般分为三种:一种是宣传教育片,这就是在中国极为盛行的主旋律电影;一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片,例如 9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娱乐电影;第三种就是具有个人风格的艺术片。我是一个老师,本能地倾向于追求能够独特表达的艺术电影。就创作而言,不论内容还是情感,只有在值得一说的情况下才应去表现,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
杨远婴:您能不能对您的艺术电影做一个更具体的描述?
谢飞:我认为,艺术电影的投资人和创作者首先以表达文化艺术价值为主旨,次要目的才是赚钱和宣教。娱乐片的功能是盈利,它所应用的技术手段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艺术片的目的就是艺术。比如说《黑骏马》,我十分喜欢小说原作,筹划近十年才得到投资。可在即将拍摄时港方投资人提出主角要用香港明星,他们认为这是个爱情故事,有明星出演会带来好票房。我反复思考后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这与创作初衷出入太大。我对他们说,《黑骏马》的故事很单纯,它只能是一个艺术片的格局。这样的影片即使用了明星,也不可能卖座,你要想挣钱,就另换一个故事去拍好了。艺术片在功能和手段上与其他类型的电影就是不同。我拍的六部艺术片都是想表达自己对社会和艺术的一些想法,都没有把票房利润考虑进去。不过,现在拍艺术片越来越难,《黑骏马》之后,我整整等了五年,才开始有新片可拍。
杨远婴:我觉得您在着手一部影片的创作时是先从主题入手的,而不像别的导演或从类型形式,或从影像风格?
谢飞:对,因为我接受的电影教育比较传统。我始终认为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在其次,所以我的主要作品都是小说改编。只有个别影片,如《我们的田野》是原创剧本,它包含了一些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体验。其他影片大都和我的私人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当一部小说在情节立意、人物性格等方面引起我的共鸣,我就选择它为自己的电影创作对象。主题通过故事和人物来体现,出色的人物性格能引起我特别的兴趣。比如《香魂女》,故事很简单,人物却极有趣,是个圆形人,而不是单面人。80年代后我开始意识到人物复杂性在创作中的特殊作用,没有多侧面的形象,艺术就没有厚度。因此在创作中把人物形象塑造放在首位。 《本命年》《香魂女》的两个主要人物,就符合我对人物性格复杂度的要求。他们不是简单的坏人,也不是单纯的好人,好与坏非常丰富地融合在一个人物身上。
我个人的创作和社会的发展联系很密切,我的思想基本上是随着时代走的。80年代曾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在那个阶段我补了十年封闭的思想课。先拍了《我们的田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接着拍了《湘女萧萧》,从过去的故事看封建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然后我就出国访学,在美国待了一年。这一年对我个人身份地位的变化没有任何意义,但确实大大开阔了视野。回来后迎头碰上市场经济和文化转型,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创作都开始反映这种变革。这个时期我所着手拍摄的《本命年》就是想表现这种变动在城市普通人身上的反映,表现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本命年》的小说原作被某些评论家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品,可我感兴趣的是李慧泉这个复杂的人物,我以前拍摄的《我们的田野》和《湘女萧萧》都反映人性和社会的冲突,但人物性格却比较单一。90年代最突出的问题是商业大潮兴起,人文思潮退隐。在很长时间内找不到令人兴奋的思想点,而经济压力却与日俱增,我的拍摄速度大大减慢。像《黑骏马》,从 1985年相中小说,构思剧本,但直到 1995年才开始拍摄。 《黑骏马》和《益西卓玛》都是少数民族题材,我对他们的文化怀有兴趣。当然,90年代的启蒙和批判已经很难进行,艺术作品大都是粉饰太平,我选择少数民族故事也是想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异族的美德和风俗继续探讨人性问题。
杨远婴:这两部影片的现实冲击力远不如《本命年》和《香魂女》了吧?
谢飞:对,远不如。
杨远婴:算是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吗?
谢飞:应该说是。因为不论是《黑骏马》还是《益西卓玛》都不和现实直接冲撞,而且,即使我对蒙、藏文化怎样用心研究,都不可能达到深刻认识、自由探讨的水准。当然事实上也不可能对它们随意褒贬,而对大的民族问题就要更加慎重,所以基本上也就是一种歌颂。在蒙、藏文化中寻找人类理想的情感方式和伦理观念,避免现实敏感问题。
杨远婴:西藏的事就很敏感,您是怎么具体处理的?
谢飞:在前不久大学生电影节举办关于我的专题研讨会上,有人把我的创作归为三个阶段:《我们的田野》和《湘女萧萧》是纯真阶段,展现青春激情;《本命年》和《香魂女》是残酷阶段,表现复杂人性;《黑骏马》和《益西卓玛》是理想阶段,在异族那里寻找人类应有的生活方式。这个概括我很认同。我为什么会走这样一条路,其实这和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大潮流的变化是一致的。我个人很难跳出时代所划定的圈子。有些东西我积极接受,像伤痕呀、寻根呀、写实呀,等等。可有些东西我就不太接受,只能放弃。在《益西卓玛》前后,《国歌》《我的1919》 等片都曾找过我,但我都没接受,我觉得这和我个人的艺术理想相差太远,实在做不了。
杨远婴:您是从剧本上就不接受?
谢飞:对。比如《国歌》,我觉得田汉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在革命潮流中的变化:最初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出没于象牙之塔、南国剧社,国难当头依然热衷唯美艺术,学生一个个地离他而去,使他开始有所反省,转而接触现实。还有他的爱情生活充满波折。要从创作角度讲,这些东西都是最有表现力的。可当时的剧本只是在写一系列抗战前后的活报剧,这些东西的艺术价值并不大。我的职业是教书,我没义务去拍赚钱的或宣传的东西,实在没片拍我可以教书,所谓拍片的空闲对我来说其实从不空闲。
在《黑骏马》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曾想拍毛泽东和尼克松,我们这一代人对毛泽东总是怀有兴趣,而毛泽东、尼克松的历史性会聚确实有意义。但这个题材很难搞,做成宣传片没意思,可挖掘一点独特的东西又不可能,反复筹措半年多,最终还是放弃了,重新回到《益西卓玛》,去做一个可操作又有文化价值的艺术片。
杨远婴:从您的概括中看,您拍片出发点首先是一个现实的主题,其次是丰满的人物性格,那么在诸多叙事手段中,您更重视哪一种呢?
谢飞:当然是传统的戏剧式的叙事,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偏重于这些。我们是现实主义传统培养起来的,我们学到的、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东西。我的几部影片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像先锋的、前卫的、表现主义在我身上的影响都很浅。我不是说它们不好,而是自己年龄大了,似乎不可能再发生大的变动了。
杨远婴:您年轻的时候对前卫的东西有兴趣吗?
谢飞: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兴趣,像《我们的田野》用了时空交错,在张暖忻、李陀提出“电影语言现代化”之后,我们“第四代”的努力主要在于打破戏剧模式、对话电影单一局面,尝试各种新方法,如《小花》中彩色片和黑白片的交替、《生活的颤音》中的时空变化。《我们的田野》是以现在回忆过去,原来分镜头剧本中的时空跳跃将近十七八次,但后来我觉得这种构思不妥,因为在剪辑时发现时空过于散乱。“文化大革命”的过去和反思的现在交叉进行,有意思的戏都在“文化大革命”部分,人物情绪起伏大,事件戏剧效果强,可频繁交替的结果却使情节线索七零八落,观众的情绪总是被打断。最后我把它们调整缩减为七八次。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形式固然重要,但内容更重要,情节的结实与否极为关键。而且我对技巧手段使用也尽量与情节和人物统一起来,开始讲求含蓄效果。在接下来的《湘女萧萧》中技巧就不那么极端,视听语言很讲究,人物对话不多,尽量靠画面表达,但整体追求内敛。
我个人认为电影创作的基础是剧本。
目录
第一编 影视创作
塑造真实感人的人民形象
——《向导》导演创作体会
《我们的田野》导演阐述
电影《湘女萧萧》导演阐述
《湘女萧萧》创作随想
影片《黑的雪》导演阐述
重建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呼唤
——访《本命年》导演谢飞
“第四代”的证明
《香魂女》导演阐述
《黑骏马》导演的话
《黑骏马》及电影文化
《益西卓玛》导演的话
电视连续剧《日出》导演阐述
与谢飞谈电影
谈电视剧创作
拍摄上海世界博览会西藏馆主题片《幸福拉萨》导演的话
2010上海世博会西藏馆主题片拍摄提纲
谈少数民族电影创作
致《黄克功案件》导演王放放
第二编 往事与故人
读懂父亲谢觉哉
——访著名导演谢飞
我的艺术梦的“萌生”时期
——忆师大二附中
贴在书柜玻璃上的信
读懂父亲
——《谢觉哉家书》序言
家有老母
怀念张暖忻导演
追思吴天明导演
——在悼念吴天明导演的追思会上的发言
同代人的述说
第三编 电影研究
电影观念我见
——在“电影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新时期:难以忘怀的年代
战争电影的三个层面
第四编 电影节
中国电影在柏林大放异彩
是艺术,是文化,更是历史
——写在 2008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再发现第四代”专题文章前面
呼吁继续放开以电影节为首的电影文化艺术市场
只身闯戛纳
初探柏林
令人崇敬的电影节人
放看不到的电影
会唱中国歌曲的外国评委
艺术电影发行公司
在国外做评委
电影节上遇到的大师
我与“金考拉”
2020 西宁 FIRST 青年影展看片随记
从西宁 FIRST 青年影展看片谈到《重视电影的文学价值》
第五编 电影产业
发行新的中国电影
——两部影片发行的研究与其启示
中国电影转型 30 年
第六编 电影教育
《电影创作津梁》中译本序言
有问号的人生
——博士生导师谢飞教授访谈
普及教育与精英教育:新时期影视教育的新课题
——博士生导师谢飞教授访谈录
《场面调度:影像的运动》序言
《魅力剪辑:影视剪辑思维与技巧》序言
《国际影视院校联合会的历史》序言
中国传媒大学“潘桦导演工作室”系列丛书序言
1950—1960 年代的导演教学
——谢飞教授访谈录
导演教学 50 年
《影剧名家讲座听课笔记》序言
第七编 随笔
感谢文学
我为什么要写豆瓣电影记录
豆瓣观影随笔《国土安全》
再读斯文•赫定(之一)
再读斯文•赫定(之二)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