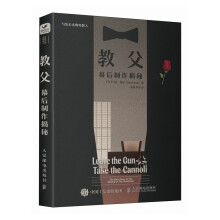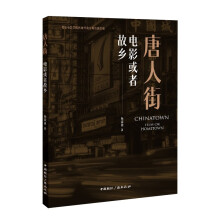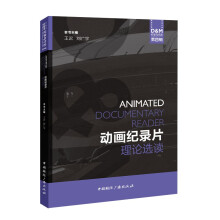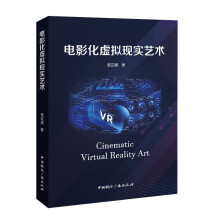《姜涛导演笔记:实践斯式体系的教学与创作》:
古里叶夫说,斯氏所发现的这些元素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它们都是生活中的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只不过是用来为艺术创作服务罢了。在斯氏体系产生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1910年以后的几年,斯氏第一个最重要的天才的发现就是发现了这些“元素”。
古里叶夫说,这些发现具有如下意义:第一,斯氏确立了创作自我感觉的各项元素,它们合在一起就能造成充分的体验;第二,由于这些元素能够分解成各自独立的单元,就有了用它们来训练演员的可能,从这里就产生了培养演员的创作自我感觉的教学法;第三,斯氏阐明了这些元素在演员的创作过程中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第四,这就又形成了创作实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抓住某一个元素就能带动其他的元素(第三点和第四点在前文所述库里涅夫专家的课堂表演训练已经给予了证实);第五,所有上述内容构成了斯氏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系”所阐明的演员的“内部技术”,也就是能够掌握演员的内心世界和体验的技术。
斯氏的这些发现是表演艺术创作与教学上的一次革命。古里叶夫说,从此演员的创作灵感问题,已不再仅仅是演员的天赋问题了,而成了可以被方法和训练所掌握的技术问题了。上述问题,也是整个“体系”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一阶段的“体系”讨论的是如何通过运用演员的内部技术,通过运用能够被分解开来的“表演元素”的训练,去获得演员正确的创作自我感觉,获得创作灵感的问题。所以这一阶段的“体系”,也被称为“元素的体系”。这并不意味着“元素”就是“体系”,更不意味着“体系”就只有几个“元素”。
斯氏获得了对“元素”的重要发现以后,又经过了20多年的不断探索,逐步对自己“体系”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了修正。第一阶段的“体系”的局限性是什么?斯氏又是如何进行修正的呢?
古里叶夫说,在1912年至1913年间,斯氏仍将创作过程主要地看作是“下意识”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的基本动力看作是“直觉”,而且将这个直觉解释为对真理的下意识的直接理解,如果意志不能激发起直觉,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人没有创作才能。斯氏当时还没有找到更为明晰的创作道路。
斯氏还将这一阶段的主要创作内容看作是创作出角色的情感,其主要手法就是引发“情绪记忆”、建立“情感的逻辑”和“激情的体验”(体验曾经有过的感情),而将“交流”理解为内在精神的过程,以为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也能进行交流。斯氏当时还以为创作过程的开头与结尾都是内在精神的体验,而且还以为只有经过情感的感受和潜入角色的内心才能达到体验。
最主要的问题是,斯氏在“体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里对于行动认识不足,以为行动只是正确体验的结果,是内心过程外露的形式。只要正确地体验、正确地感觉,就会得出正确的表现形式——行动。因此,斯氏在第一阶段的元素中把“情绪记忆”强调到了不应有的地位,而对于“行动”却没有提及。后来,行动在元素中也出现了,但是还没有被看作是物质的行为,只是被当作内在精神的意向,只是作为体验的因素而存在的。再后来,行动在元素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并最终取得了首要地位。
在此期间,心理学的成果证明智慧、情感、意志在人的身上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只能存在于有机、完整的行动之中,而且只有在行动之中才能发挥出它们的作用;了解一个人,不是通过他的情感与感觉,而是通过他在各方面的活动,因为活动之中就包含着他的情感和感觉。所以,到了1936年斯氏再次修订《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时,“行动成了最根本、最主要的元素,成了创作自我感觉诸元素中第一个元素”。
斯氏还得出了他的有名的公式:“心理技术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唤起创作器官的一切元素,使之行动起来。”所以说,行动不仅是一个主要的元素,同时也是创作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情感的逻辑”也必须融合在行动的逻辑和顺序里。只把行动看作是内心的意向就不够了,必须要把行动体现出来。内在的东西必须获得外在的表现,精神的行为也必须要通过形体的行动表现出来。
斯氏发现了:行动,是心理行动与形体行动的统一。
古里叶夫说,当斯氏获得了这样的认识以后,不仅在讨论行动时必定要讨论形体行动,而且他也说明了形体行动本身就是能唤起“真实感”与“信念”的刺激手段。斯氏还用极为鲜明的公式说明了行动的最高作用:“在舞台上应该行动。行动、能动性,这就是戏剧艺术的基础。”在这一阶段的研究过程中,斯氏还提出了“最高任务”与“贯穿行动”的学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