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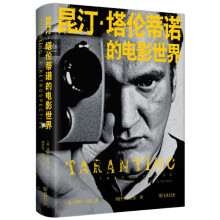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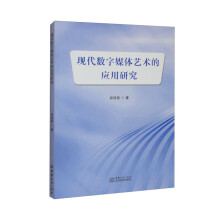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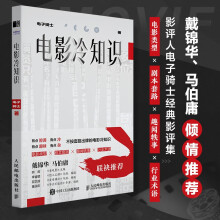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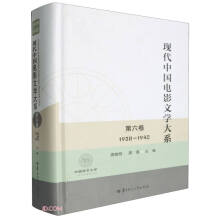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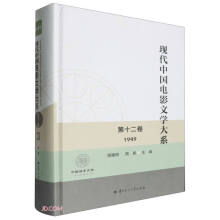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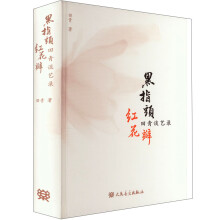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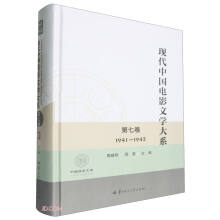
本书力图从理论的高度、思想的厚度和批评的锐度进行影视艺术批评建构,研究从高处着眼、低处入手,探寻影视艺术在新世纪以来发展变化的具体规律,对新世纪中国电影类型变化与特征、影视艺术与国家形象建构、西方影视文化理论与影视现象、中国当代电视文化批评、媒介融合与影视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进行深入思考,体现出了作者独到的批评视角和思辨理念,此外本书还对一些经典理论大师和理论成果进行了再思考、再批评,对于影视艺术理论的发展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同时,本书研究媒介融合视域下影视文化生态的变化、影视现象的解读,不仅在文本细读中下足功夫,还能够充分还原文本的创作背景和发展链条。特别是在技术赋权的时代环境下,探究传媒技术的发展对传媒文化、传媒生态、传媒艺术、传媒接受等带来的深层影响,并保持对这些影响的价值追问,从而为读者客观看待影视传媒现状提供前沿视野和学理思考。
第一章
分化与重构:新世纪中国类型电影新变
青春类型电影的“萌”文化
爱情题材电影的类型融合与元素弥散
新都市电影的名流效应商品化现象
第五代导演古装类型片的传统意识重构
女性题材电影类型的成长主题裂变
第一节青春类型电影的“萌”文化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不同媒介文化在形态和风格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其中,尤以高度年轻化的互联网文化对传统影视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最引人注目。主要由青年网络用户构成的(亚)文化群落所呈现出的活力,已经成为主导中国电影审美形态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叶凯:《二次元文化对当下中国电影审美倾向的影响》,《当代电影》2016年第8期。在形形色色的互联网(亚)文化形态中,基于“二次元”文化的“萌”元素无疑是最为活跃的一种,它借助其爱好者强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能力,极为有力地介入了新世纪中国电影工业的生产,成为电影美学领域富有阐释价值的审美对象。
中国青春电影的“萌”化并非影像或叙事风格的简单叠加,而必须置于互联网时代文化艺术边界坍塌、交互融合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究竟什么是“萌”文化?这种文化以什么方式参与到当代青春电影的美学光谱之中?“萌”文化的介入又对青春类型电影有哪些潜在的影响?本节通过全面地梳理和深入地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从而为中国新世纪媒介文化的融合趋向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一、“萌”文化及其意涵
“萌”文化源于在网络空间拥有大量拥趸的“二次元”文化。这种源于日本,盛行于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文化形态大体指以动画、漫画和电动游戏(ACG)为主要载体的幻想性叙事文本。“二次元”一词,通常被用于将这类叙事作品与三维空间里的真实世界区分开来,其文化功能在于令消费者产生一种逃避、遁世、隐居的快感,并借此来回避真实的社会问题。沉迷于“二次元”世界的年轻人群体有时被称为“御宅族”(Otaku),这是一个来自日语的词汇。调查显示,御宅族的社交生活是高度网络化和虚拟化的,中国的中度、重度互联网用户约占该群体总人数的近90%,他们不但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缺乏兴趣,而且对现实主义基调的虚构流行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也不屑一顾,而对被其视为“萌”(大约相当于可爱的、讨人喜欢的)的二维卡通人物有着一种近乎拜物教式的迷恋。易前良、王凌菲:《青年御宅族的媒介使用与亚文化取向研究》,《青年探索》2011年第4期。在互联网的世界中,二次元文化拥有自己的“阵地”,如美国视频网站Crunchyroll,以及中国的AcFun(A站)、Bilibili(B站)等,这些平台如今已拥有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
在日语词源中,“萌”大约有“小而可爱”的含义,其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与日本传统文化“以小为美”的美学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借助二次元文化在东亚流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萌”也成为其庞大的爱好者群体的一种共通的审美旨趣。与传统审美体系不同,“萌”更多形容的是一种主观感受,而非客观标准,它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因此,不同的人会对“萌”这一概念生成各自不同的物理特征和精神气质的对象。朱岳:《萌系御宅族的后现代性状》,《东南传播》2008年第12期。从来源和构成方式上看,“二次元”爱好者群体所普遍推崇的“萌”属性,其本质是一种接受美学,意即这一元素的文化能量首先是在接受(reception)而非生产(production)的环节生发和释放的。由于二次元爱好者群体在中国年轻互联网用户中的比例极为庞大,且主要集中于12-30岁的年龄段,被认为拥有强大的网络活跃度和文化消费能力,因此,“萌”元素在中国流行文化工业领域具有日趋显著的影响力,也便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由于目标受众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合性,‘萌’文化与青春、都市、幻想等类型的影视作品不可避免产生了关联,从而使得‘萌’元素日趋成为这些类型的电影受众的一种主流的消费-审美对。”齐伟、李佳营:《论华语电影的二次元审美文化现象》,《电影艺术》2016年第5期。例如,电影《匆匆那年》中对经典日本动漫作品《灌篮高手》中若干场景的交叉剪辑以及对其主题歌的借用;《捉妖记》对真人、CG制作模式的成功采用以及对主人公“胡巴”形象的明确“萌”化设计;《万万没想到:西游篇》被研究者视为“90后二次元动漫的3D视觉化呈现”陈露露、胡铁强:《“二次元”渗透下电影的审美趋势》,《戏剧之家》2016年第6(下)期。,等等。不过,比起以CG形态或拼贴(bricolage)方式进行的硬性“萌”元素植入,将“萌”元素完全内化,从而巧妙地隐藏在人物塑造、剧情推进和冲突营设之中,显然是“萌”文化深度介入甚至改造传统电影风格的佐证。这种结合方式在面向年轻城市白领和在校大学生的青春类型片中得到精确体现。例如,“萌”文化所设定的各种审美对象的类型,包括“萝莉”“正太”“大叔”“软妹子”“男闺蜜”等,在《致青春》《何以笙箫默》《滚蛋吧,肿瘤君》《我的少女时代》《失恋33天》,甚至年龄向更大一些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中,都有鲜明的存在感。
总而言之,“萌”元素对中国新世纪青春电影的介入,虽是基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毕竟“二次元”爱好者拥有庞大的规模和旺盛的文化消费能力,但最终却“改造”了青春电影的接受美学类型。如同“二次元”的本意是将复杂的三维世界扁平化、简约化一样,青春电影也通过对“萌”元素的有意识的使用而实现了对人物、情节和意义的标签化,从而使这种类型的电影在最大程度上被赋予一种类似“都市童话”的美学气质,使在三维世界里被权力和资本裹挟的复杂人类情感转化为一种纯粹的审美体验,进而令观众获得遁逃的快感。一如有学者评价的:“‘萌’是一个共同妄想论者的自由世界……迫使人转向想象的世界,在想象的世界里体验何为纯爱。”姜建强:《萌是什么还将是什么——日本萌文化的一个趣点》,《书城》2016年第3期。
第一章分化与重构:新世纪中国类型电影新变/
第一节青春类型电影的“萌”文化/
第二节爱情题材电影的类型融合与元素弥散/
第三节新都市电影的名流效应商品化现象/
第四节第五代导演古装类型片的传统意识重构/
第五节女性题材电影类型的成长主题裂变/
第二章现象与产业:新世纪中国电视文化批评/
第一节文化类真人秀节目中的传统文化传播/
第二节流行影视剧中的青年文化书写与“青年性”建构/
第三节电视文化的仪式重建与情感共同体凝聚/
第四节高概念电视节目的产业创新与文化博弈/
第三章自塑与他塑:影视艺术与中国形象塑造/
第一节“球土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身份探析/
第二节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建构主义取向/
第三节中国电视文艺创作中“国家形象”的表意实践/
第四节外国影视纪录片对“中国形象”的文化认知与建构/
第四章跨界与融合:媒介融合与影视文化传播/
第一节文学的跨媒介传播现象探析/
第二节流媒体影视文化生态的悖论与弥合/
第三节中国网络剧的戏剧性叙事强化与全方位表达/
第四节中国视听综艺生产的戏剧性转向/
第五节中国满族民俗文化的影像化传播/
第五章探索与争鸣:电影理论探析与域外电影评介/
第一节情动转向:后批评时代电影理论建设的一种可能/
第二节符号的“空无”:罗兰·巴特的隐喻世界与东方电影的意象
构成/
第三节隐喻 象征 神话修辞:电影文本认知的一个重要视域/
第四节叙事 镜像 解构:系列惊悚电影《死神来了》的叙事策略与
文化意识/
第五节反思 和解:朱迪·福斯特导演女性视角下的电影创作观念
解读/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