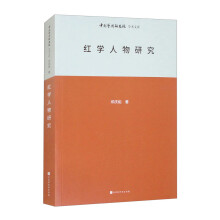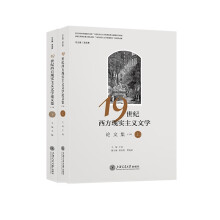在浩阔壮美的秋色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正在北京举行。鲜艳的五星红旗辉映着蓝天白云,如一团火焰、一片红霞,徐徐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用最准确、最豪迈的语言宣告了旧制度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启。
但,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停下铿锵的脚步。战马嘶鸣,兵车辚辚,刃带秋霜的刀剑指向西南边陲。因为在那彩云之南,还有不曾解放的土地,还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还有系及新生共和国安危治乱的特殊战斗。
在哀牢山以西的滇西南地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的山水奇观。一座座山像春笋出土,直指云端;一条条河像篾箍爆裂了的水桶里的水,恣意流淌。群山众水衍生出丰富无比的各类动物、植物,使这一带成为享有盛名的地球生物基因库。似是天人感应,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着众多的民族,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生存方式,拥抱着日月星辰,跋涉在春夏秋冬,耕耘着山水田园,演绎着人间传奇。
时令已是冬春之交,北国草枯木凋,但这里的山山岭岭上,葳蕤的枝叶完全没有衰败的样子,依然像染了色一般苍翠生碧。远远近近或高或低、或隐或显的峰峦,相拥着、层叠着,如海浪奔涌,逶迤远去。
没过人顶的茅草,茎粗叶阔,放肆地、狂野地生长着,密密匝匝,连老鼠也很难钻得进去。只有当刚劲的风卷过来时,才会被看不见的巨手推得一片片地向一边偃倒。茅草丛里,有一张显得刚毅有力、非常年轻的脸。嵌在脸上的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正透过纷披的野草,像探照灯一样,向远近不停地扫视。他抬头望了望快要压着山顶的太阳,眼神里溢出明显的焦灼,宽大平滑的额头挤出一道道浅浅的皱纹。
当他再次用鹰眼一般的目光向四周搜索时,眉毛上方浅浅的皱纹骤然间像绳子一样拉紧了,整个脸上的肌肉绷紧得像鼓面上的牛皮。视野里有他正苦苦等待和寻找的目标:不远处一条不大宽的河流的木桥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在快速行走。
草丛里的潜伏者用力地抿了一下厚厚的嘴唇,不由得抬眼看了看已经转身返回寨子的十来个同伴,要不要呼唤他们回来,一起参与即将进行的猎杀?但他瞬间如同向山涧扔石子一样扔掉了呼唤同伴的念头。因为喊声出口,就是自己示弱示怯。这万万不行,即使自己的脑袋被对方砍了,也不能像懦夫一样犹豫、退缩。况且凭着自己的身手和所处的有利位置,只要一出刀,对方瞬间便会像斫断了的篱笆桩一样倒下。他还算计好了:猎杀一个,吓走一个。于是,他紧紧握住手中锃亮的长刀,拨开野草,压低肌肉发达的身子,赤着的脚带着风,像猎豹一样跳跃着,快速地向桥头靠近。
桥上的两个年轻男子越来越近。当前面的男子走到桥的尽头,准备跨步登岸时,正等在桥头的持刀人像青蛙跳水一般冲了出来,手中的长刀带着光影和风声挥了过去。
走在前面的男子在慌乱中闪身,躲过了致命的一刀,但随着身子后仰,脚下一歪,“噗通”一声掉进河里,激起一蓬很高的水花。
持刀人便向另一个男子进刀。这个男子已经快速掏出了手枪,但没有来得及推弹上膛,刀刃已像吐着信子的蛇一般连连在眼前晃动。
掏枪人一面敏捷地躲闪,一面以手枪招架。
“哐当”一声,刀口撞在了枪身上,如果是暗夜,一定会有火星飞溅。手枪脱手,斜着向天空腾跃了一阵后,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迅速下坠,跌落桥下,掉入水中。
持枪人虽然已是赤手空拳,却并不慌乱,更没有恐惧。他猛地沉腰下蹲,一只手按在桥面上,一条腿下卷起旋风,划出半个肉眼看不见的弧形,来了一个扫堂腿。持刀人并没有中招,他身随腿动,敏捷地后撤了半步,躲过了这重重的一击。但持枪人收腿后,没等持刀人再次挥刀,便做了一个难度极高的僧人撞钟动作,一只脚像流星锤一般落在了持刀人的手腕上,长刀带着杂乱的白光,飞出很远,然后追着手枪的轨迹,掉落桥下,斜插在了河中的浅滩上。
持刀人在桥上摇晃了几下,站立不稳,似是刀鞘靠向刀身,追着那长刀掉入河中。
持枪人用力吸了一口气,弯腰伸臂起跳,如一只捕鱼的水禽发现了目标,猛地扎进水里。
双方怒目相对,在近岸的浅水里进行着殊死搏斗。你来我往,拳脚交并,口中还发出时轻时重的单音节声响。
持枪人最终将持刀人制伏在河滩上。
先前掉下河的男子拔下几棵长在路边的野麻,麻利地揭下外皮,快速搓成一根好几尺长的麻绳,将持刀的攻击者双手反剪、绑牢。
三人一路快行,进入一座民居。
解放军某师副政委兼独立团团长张钧山在屋内踱步,他标准的国字型脸上带着思虑和企盼,不时把目光移向门外。
当他瞥见这三个人的身影时,立即快步来到门边,喊着:“云良、小石,你们可回来了。”
连长杜云良行了一个军礼,晃了晃缴获的长刀,声音响亮:“报告团长!今天去沧西县城侦查回来的路上,遇到这个人持刀突然袭击,最后被我们擒住押了回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