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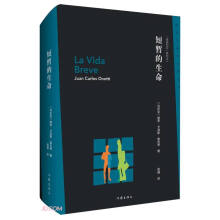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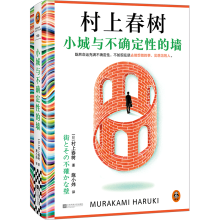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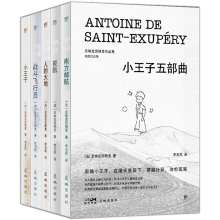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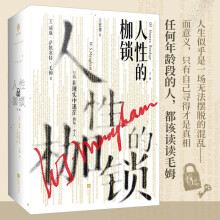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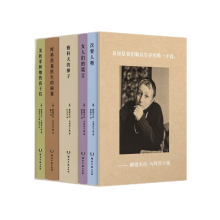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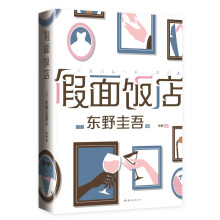
巴黎丽兹酒店由“世界豪华酒店之父”的凯撒·丽兹创办于1898年。一百多年来,这座豪华宫殿始终是大艺术家们的流连之所。法国大文豪马普鲁斯特,时尚女王可可·香奈尔,美国大作家海明威、菲兹杰拉德、杜鲁门·卡波特都曾是丽兹酒店的座上客。著名的香水大亨塞尔日·鲁腾斯长期租住517套房,畅销书作家丹·布朗也曾在《达·芬奇密码》中数度提及酒店的华美和雍容。现在,让我们化身为故事的女主人公——拥有贵妇和间谍的双重身份的布兰琪——在这座举世无双的华贵宫殿中尽情探险吧。
莉莉
布兰琪死了。
“死”有时反倒是一件幸事,我觉得对布兰琪来说就是这样,因为她生前是那么鲜活明媚,当她的生命戛然而止时,定格在我脑海中的,永远是那个活力四射的形象:布兰琪唱着水手的歌,手背上稳稳地托着一杯香槟酒;布兰琪向街头的妓女演示怎么跳查尔斯顿舞;布兰琪对待一个不值得给好脸色的人温暖如春;布兰琪倔脾气发作,一扭身,一跺脚,像个孩子。
布兰琪嫉恶如仇,傻乎乎地反抗得罪不起的人。
然而,关于她的记忆,最清晰、最生动的,是第一次见到她在那个最适合她的地方:丽兹,她心爱的丽兹。
1940年,纳粹来的那天,她还在路上,正从法国南部赶回来,还没到家,但她向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形。
一开始,丽兹的员工和客人只听到他们的声音:一路轰鸣的坦克和呼啸而来的吉普驶入那个巨型广场,围着方尖碑停下(拿破仑雕塑站在高高的碑上,惊恐地俯视着脚下);随后传来靴子的金属后跟叩击鹅卵石和人行道的声音,一开始隐隐约约,继而越来越响,德国人来了,一步一步逼近,他们快到门口了。丽兹的员工和客人两只手绞来绞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人冲向楼下的员工通道,但没能跑多远。
里兹夫人,个子小小的,仪态万方,穿着她最好的一条黑裙子,还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款式,她候在自己家的大门内。她的家,就是这座全巴黎最豪华的酒店。她双手在胸前交握,那两只佩戴着珠宝的手一直在抖。不止一次,她的目光瞥向那幅挂在上方的巨幅肖像,似乎亡夫的肖像能告诉她该怎么做。
有些员工从1898年起就跟着她——还有他——直至今日。他们还记得开业第一天的盛况:这几道门突然间敞开,衣着光鲜、满面春风的宾客首次踏足富丽堂皇的“大殿”(对,里兹先生的新酒店没有“大堂”,他不想让“庶民”有流连之处,因为这会令金碧辉煌的酒店正门失色),都无法掩饰惊叹的神情。这些客人,不外乎王公贵族、阔老钜子,或者像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莎拉·伯恩哈特那样的社会名流。然后,乐师奏响音乐,枝形吊灯熠熠生光,厨房里送出一道道出自奥古斯特·埃科菲之手的精品——点缀着薰衣草和紫罗兰糖渍花瓣的香草糖霜蛋白甜饼、罗西尼牛排、肥美的肉酱,甚至还有以奈丽·梅尔巴夫人之名特制的梅尔巴氏桃子冰激凌(她已经答应为宾客献唱小夜曲)。他们最后整一整自己的新制服,绽开笑容,带着满腔的工作热情,搬啊,擦啊,切啊,剁啊,掸啊,安抚,宠溺,各尽所能。他们兴奋极了,为自己能参与这家豪华的新酒店开业——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带独立卫生间、每间客房都配电话、引入新的电灯照明、全部用电灯替代传统煤气灯的酒店。
旺多姆广场上的丽兹酒店。
但今天,他们没有笑,有些人甚至还在德国人闯进前门的那一刻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这些德国人挎着枪,沾满尘土的黑靴子玷污着地毯。他们没有摘下帽子,那盛气凌人的带鹰徽的帽子。灰绿色(四季豆的颜色)的军服,在门厅耀眼的金色、大理石和水晶,墙上华丽的挂毯和铺着地毯的大楼梯那雍容的帝王蓝的映衬下,显得丑陋又粗鄙。
他们胳膊上那截血红的袖章上爬着一只凶狠的黑蜘蛛——卐字——在场的人无不瑟瑟发抖。
德国人来了,正如大家听到的那样。在法国军队像埃科菲先生的精致酥皮糕点一样溃散之后,在事实证明马其诺防线不过是小孩子的幻想之后,在英国盟军抛弃法国、在敦刻尔克越过英吉利海峡溃逃之后,大家都听说德国人要来了。真的来了,他们就在这里,在法国,在巴黎。
旺多姆广场上的丽兹酒店。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