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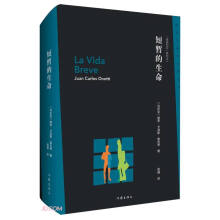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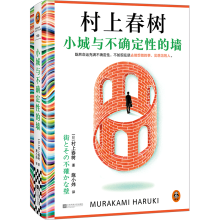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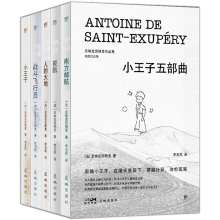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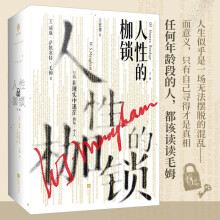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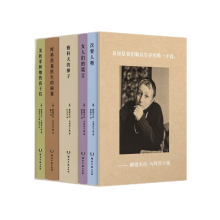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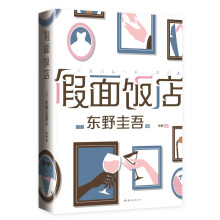
这下她回来住了,镇子看起来不一样了。她完全习惯了把基列当作怀旧的对象和背景。只有杰克除外,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喜欢回家来,而他们也很乐意再次离开。旧地旧时的故事于他们是如此的亲切,而他们又离得有多远,散落在四方。留在旧地的昔日,是件非常美妙的东西。但现在她回来了,照父亲的说法,住下了,却让记忆变得可怕起来。任记忆越过界限朝这头蔓延过来,成了现时,可能也成了未来——他们都知道,这是件令人痛惜的事。想到他们的怜悯,她心里难受极了。
大多数家庭拆除外屋卖掉牧场已经很久了。在那些房子之间冒出来不少新近式样的小房子,让老房子看起来越来越不相称了。基列的房子曾经矗立在小农场中,有园子、浆果丛、鸡屋,还有柴草棚、兔子窝,牲口棚里养着一两头牛和一两匹马。这些只是生活的必需品。是汽车改变了这一切,父亲说。人们无须像过去那样自给自足了。这是一种损失——没有什么能像鸡粪那样让花儿长得旺了。
什么东西都留存着的鲍顿一家,也保留了他们的土地,空空的牲口棚,无用的柴草棚,无人剪修的果园和没有马的牧场。在那片永远不变的童年的土地上,哥哥姐姐们能够也的确细细地记住了那些日子。他们各自都拥有记忆,不过更多时候是大家拼凑起来的记忆,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按个人分配开来。他们翻看着相片,温习着旧日时光,笑着乐着。父亲也非常的高兴。
鲍顿家的土地在另一幢房子背后。那幢房子位于绵延两条街区的宽阔地带上,小镇人口增加,扩张成了街区。有个邻居——他们仍旧叫他托洛茨基先生,是因为当时从大学回家的卢克这么叫他的——有好些年,在鲍顿家一半的土地上种了苜蓿。有时候父亲想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他对这件事的不满。“要是他能问我一下就好了。”他说。当时她还太小,没法理解苜蓿暴动事件。等她到了大学,才开始明白老故事其实是在别处已经熊熊燃烧过的余火的一点点动静和烟雾。想到基列是她读到的全世界的一部分,这让她高兴。她真希望自己认识托洛茨基先生和他的妻子。
不过,她大二结束时,尽管他们年纪挺大了,也还是出于一时的愤慨离开了基列,将基列留给它的蠢行,但没人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成了战场的那块土地,如果邻居没有耕作的话,原本也是不会被利用的,再说种植苜蓿也有利土壤。可笑的是——或许也是事实,邻居似乎没有工作,也反对金钱交易关系。他将庄稼捐给了一位乡下的表亲,那人回礼赠给他一笔钱。不管怎样,父亲怎么也没法说服自己去提出抗议。更何况邻居是个不可知论者,很可能正一心想找个道德伦理上的话题争论一番。那次,父亲想阻止镇上穿过他家的土地铺路。他没什么好的理由,只不过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如果在世,都会反对这件事。经历了那次尴尬之后,父亲似乎觉得他不能在这类的争论中再失败一次了。他醒悟到这一点是在一个漫漫长夜,也没有再细细想一想,他对自己的正义立场的信心像薄雾似的散尽了。就是在那一刻,晚上十点稍微过一点儿,他醒悟过来了,接着是黎明之前的七小时。他的事到了白天看起来也没好多少,于是他写了封信给镇长,简单而有尊严,一字不提“一毛不拔的伪君子”这一说法——他是在结束了一段自认为挺愉快的谈话走开后,觉得听到了镇长在他背后这么咕哝的。吃晚饭时,他把这事告诉给所有的孩子听,而且不止一次地在讲道时作为例子引用,因为他的确真诚地相信,当上帝给他道德上的指示时,不仅仅为他一人所用。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