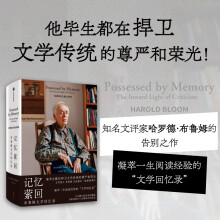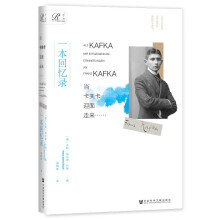《张爱玲 最是清醒落寞人 珍藏版》:
港大新生
1939年夏天,各地战火纷纭,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人人自危,但张爱玲在恐惧中却有一丝欢悦,因为她终于可以逃离让自己伤痕累累的上海,来到香港读书。虽然未能踏上魂牵梦萦的英伦土地,但香港那如明信片般清亮蔚蓝的海水还是让张爱玲的心情舒畅不少。
那时的香港既是学子们的避风港,也是文学青年的天堂。“避风港”是因为那时由于诸多原因,战火尚未烧到这里;“天堂”则是因为“七七事变”后,茅盾、夏衍、于伶、萧红、戴望舒等一大批知名作家避难至此,他们或办报纸杂志,或潜心著述,造就了一个短暂而繁荣的香港新文学时代。有趣的是,后来在张爱玲生命中写下重重一笔的胡兰成,彼时也活跃在香港文坛,以轻盈的“流沙”为笔名,任《南华日报》主笔。当然,他们此时并不相识。
虽然张爱玲幼时从上海搬至天津又迁回上海,没少奔波,但搬来搬去终究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这次香港之行却是她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母亲和姑姑不放心,便拜托姑姑张茂渊在香港的好友李开第先生做张爱玲的监护人。让人感慨命运神奇的是,多年之后,张茂渊亦在李开第患难时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最终两人结为夫妻。1980年,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得知张茂渊和李开第境况不佳,便将自己在国内的著作版权交由李开第先生处置,所得稿费也一并赠予这两位曾悉心照料过自己的至亲老人,传为佳话。
和亲人关切造成的精神上的压力不同,香港大学的同学带给张爱玲的压力则是物质上的,他们多来自富贵人家,出手阔绰,这是靠着母亲有限资助的张爱玲所不能比的。一位华侨之女在得知开战的消息后,惊呼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怎么办?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无法理解战争,自然更无法理解张爱玲的苦涩。
所以,在学习上向来懒散的张爱玲延续了复习留学考试时的勤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期望用奖学金减轻母亲的负担。况且,港大的优秀毕业生还有去英国留学的机会,虽然不知那时欧洲的战况如何,但张爱玲心中的“英国梦”却从未熄灭。
张爱玲在港大读的是文学专业,许多教授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西方文学的教授喜欢莎士比亚,每每讲到偏爱的情节,他总会陶然忘我,甚至趁兴点一根雪茄。教古典文学的则是一位颇有仙骨的老先生,他吟咏的楚辞能让张爱玲听见战国楚地的苍阔悲歌,他念诵的唐诗能让张爱玲看见长安街头的熙熙攘攘……当然,期末时张爱玲也给他们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因为张爱玲门门功课第一,是个十足的“学霸”。当然,当学霸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休闲活动的大幅缩水。
也许是距离稀释了旧日苦闷,也许是缺少娱乐的生活让张爱玲略感郁结,张爱玲时不时会思念上海的家,思念母亲和姑姑。她们彼此通信甚勤,母亲的信里满是关切与叮咛,姑姑的信则充满诗意文采。为了加强英文水平,好为将来留学做准备,张爱玲总是试图以英文写回信。但她渐渐发现,在留过洋的母亲和姑姑面前,自己的英文水平实在不够用,所以她的回信总是越写越短。因此,张爱玲在繁忙的功课之余,用原本写小说散文的时间补习英文。
其实,张爱玲苦学英文还有一个野心,那就是将来能像林语堂一样,用英文写出一流的作品。从这点来说,她从未远离文学。
张爱玲对汉字的嗅觉并未因英文的阻滞而变得迟钝,入学一阵子后,张爱玲看到上海的《西风》杂志以“我的……”为题悬赏征文,首奖500元。“见钱眼开”的张爱玲抽出空来写了《我的天才梦》寄去。这篇奇文以“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开头,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作结,中间夹杂几则轻描淡写却相当生动的旧事,文辞惊艳又不乏深刻自剖,所以斩获了这次征文的首奖。但让张爱玲失望的是,所谓“首奖”并非一人,而是13个人,在13位获奖者当中,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她被排在末尾,只拿到很少的奖金——虽然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书时正是以《天才梦》为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