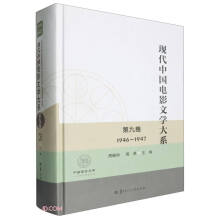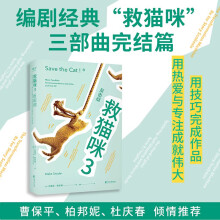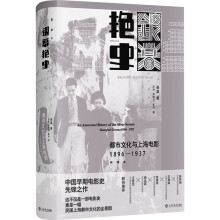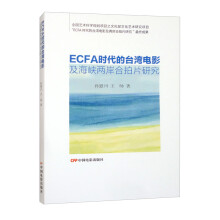7.电影之眼
在两个时空里,导演设计了种种联系,但是又不让这些联系过于一一对应。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人类开始测量时,他们就失去了乐园。当人类自觉于自身,并将自身作为尺度时,人类就失去了空旷的世界,被局限于有限的空间之中。电影里,酒店的走廊与房间成为成年人活动的主要场景,鸟鸣是手机设置的声音。在追求美丽新世界的路途中,人类建造了一个又一个废墟,就如本雅明所说:“面对废墟,被大风吹向未来。”
当仇晟在电影里试图呈现这样的世界图景时,或者说试图在电影里建造起这样的世界图景时,他怀着的是一种感伤的对照、一种返回的渴望。(在电影的最后,成年的夏昊又回到林中,他用小溪的水洗脸,与朋友躺在草地,说着方言。有趣的是,与他一起重返的是一个同事,而不是恋人。爱情是电影中一种对集体的破坏力量,友情更具备乌托邦的美感)同时,他又表现出一种隐秘的、建构的成就和索隐的乐趣。
这部电影的主题虽然严肃,却带着点游戏的性质。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在玩游戏,大人也有一个玩游戏的段落,而平行宇宙,时空交错,也像是个游戏。当望远镜从一个时空跌落到另一个时空,色调变幻,音乐迷离,这几乎就像是在游戏中解锁了一样道具。导演用视听语言来组织这个游戏,他就像一个填字游戏的制作者,留出暗示和空白,并且不给予所有的答案。每个人得到的答案是不同的,因为可资对照的经验、可资探讨的观念,每个人并不相同。文本的开放性,并不只体现在结局上,更体现在过程中,留出多少可以进入的缝隙。与“缝合”得特别完美的叙事、给观众一个白日梦不同,《郊区的鸟》让人不能轻易入梦,而在现实与梦之间,在物质性与语言之间,在叙事与观念之间,每多徘徊。诸如拍什么、为什么拍、怎么拍这些问题,都像是建筑的承重结构与管道处理,并不完全隐藏,让人不能不去思考。
在童年与成年、时空的平行与连接这些重心之外,这部电影还有一个重心是关于电影本身的:电影如何成为一个虫洞。片尾的地下隧道里,有孩子们的涂鸦如史前壁画,地下水渗透的声音如时针,那一刻,我们存在于一个重叠并置的时空里。隧道的幽暗、幽深,是一个虫洞的天然喻体。而与隧道相近似的,是镜头。镜头在这个时空里截取了一个圆柱体的视域,也如同一条隧道、一个虫洞。从观测器的镜头望出去、从望远镜的镜头望出去——电影中多次给到圆形构图的画面,这是电影之眼,是它对时空的观察、呈现与建构。电影的最后,成年夏昊用望远镜望向密林深处,孩子们列队走过,这一瞬间的感动,既是对时间的致敬,也是对电影的致敬。
与祝新探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不同,仇晟更倾向于探讨“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终归无解,对现实机制的不信任,只能转向对童年情境的心理陷落。电影是一个美妙的工具,它将时空扭结,对接起陷落与慰藉。但如果平行时空如永恒的巨大蛛网,那么在无限的时间里,对世界的摸索与观测,在世界中的游荡与着落,那些偎依与忧惧,都只能成为审美的客体,行将失去本体的意义。这是《郊区的鸟》的危险所在,电影之眼成为主宰,时间的谜题飘散在风中,人类最终在某个甜美的时空情境中找到栖身之所,如同郊区的鸟。而这鸟声,是自然的,还是模拟的?抑或是数字的?
8.在路上
在此时此刻谈论“杭州新浪潮”,我们就像是才抓了三张牌,就想赢下这一局的赌徒。它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虽然彼此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却也有可总结的共性。他们的经验里没有太多物质与精神过于匮乏带来的紧张与创伤,他们的电影指向审美与哲学,都尽量真诚地对待自己的经验。在电影诞生有一百多年的今天,年轻的创作者多是在迷影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三位导演的本科专业都不是电影,但他们在观片、拍短片、参加创投、参加影展中完成了自我教育,成为一名电影作者。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视听产品与消费品已如此丰富,成为一个电影作者,几乎可以与成为一个诗人类比。站在流量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反面,寻找那些真的与深的东西,需要更沉潜地体会与更主动地思考来对话的东西。杭州新浪潮的这些电影,有一种共同的诗意,它们对空间与时间的感知、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感知、对内心的感知,最后形成一种流动的叙事中的“情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