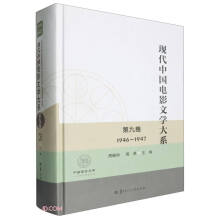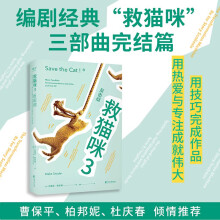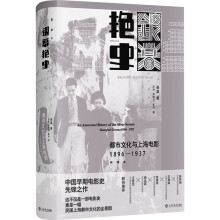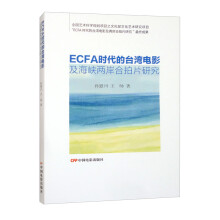如果说李红的镜头里呈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从乡村来到城市寻梦的人们的经历及记忆,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浮萍般在都市与乡村间来来去去,更多的人都如《回到凤凰桥》《远在北京的家》等片中的打工者一样,顺从于命定的轨迹回到原有生活中,都市的一切最终只能定格在粗糙的影像里并成为人生记忆的底片。那么,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以更急切的步履向前推进的时候,有一部分都市的外来者并不像最早期的过客那样只做都市的浮萍。相比之前的外来者,他们更渴望能够在都市真正立足,尤其是让他们的第二代能够融入都市,并获得都市的认同。底层的流动人群,他们脆弱却又坚强得如尘埃一般在都市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2002年汪士卿的影片《像灰尘一样飞》,便直接呈现了这个群体如飞尘般的生命状态:1983年,一位叫唐家荣的四川姑娘在17岁时被人贩子卖到山东,与一位比她大12岁的男人结婚并有了孩子。在唐家荣32岁时,她决定结束原始的耕种生活到北京打工。唐家荣在北京打工的日子里,经历着和打工的乡村女子共同的漂浮和艰辛:唐家荣洗过碗,也卖过杂货,在2000年唐家荣认识了卖花的江苏小贩老王,老王教她鉴别花的品种、到花市买货并开始各推一辆车开始了与城管打游击的卖花生涯,一段时间后,老王与她生活在了一起。但对唐家荣来说,与老王的同居生活并非长久之计,一直支撑着她艰苦打工的力量来自心底最隐秘的期望,这就是将原来的“老公”与儿子接到北京,然后一起定居北京。影像里唐家荣的生活与她的本真生活一般粗糙,甚至因其真实和直接而更具震撼性力量。唐家荣与丈夫、孩子在北京团聚的愿望更像海市蜃楼一般遥远,更何况,不仅在都市的身份不被认同,唐家荣甚至连乡村里的身份都模糊难辨,她没有“结婚证”。无论在都市还是在乡村,身份模糊的唐家荣都如灰尘一般模糊和卑微,也如尘土一般坚忍,但她那微弱的力量,却反证着时代的印迹。
二 工业空间的零落侧影:《铁西区》与时代记忆
工业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命题,而“城市”,在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语汇里,它通常与工业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业空间成为转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集散地,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城市和当代中国的提喻”①。作为都市重要构成部分的工业空间,其起落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映射着社会变迁的动态图景,也因此,关注以工业空间为主题的影像亦成为辨析社会记忆流转脉络的重要线索。
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里,流行文化、偶像文化尚未兴起,工人群体是主流都市影像呈现的主要客体,典型的如影片《铁人王进喜》,就呈现出工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意气风发的状态。重工业区作为大工业时代最重要的代表性空间,出现在绝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有关都市的诠释影像中,工业大生产的热气欢腾场景、喜悦而自豪的工人群体、代表集体利益的个性模糊的代表性人物形象、热情昂扬为基调的配乐构就了此类都市影像的基本要素,并以此营造出相对单纯和欢欣的时代记忆。但90年代国内的工业改革及全球化背景下商业及资本的大举侵袭,使原有的社会空间结构体系发生巨大改变,新兴的市民阶层替代工人阶层成为都市的主体力量,以金钱为导向的消费社会价值模式导致个人主义进一步蔓延。而工业空间在现代技术语境下更多地与数字、信息技术化联系在一起,数字时代的工业空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以劳力为代言的工人所能掌控和主导的。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后,东北某些地区大量工人下岗,但与其社会地位的迅疾变化相对应的奇怪现象是:此阶段工人再次以主体形象频繁出现在众多影像中,“甘当革命螺丝钉”的口号被转移到鼓励自主创业的语境里,昔日高扬集体精神的主人公开始被强调靠个体智慧获得经济自由,并出现了众多宣扬个体创业的影像。在这样的影像里,成功创业的工人以全新形象重新解说和阐释了商业时代的新生活。在此类影像中,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工人形象被具有商业才能的个体概念替换,或者说,对工人创业的关注热度覆盖了工业空间的冷落情景。若在此背景下搜寻独立纪录片构成的社会记忆版图,王兵在2001年完成的《铁西区》则以其鲜明的时代记忆印迹从众多影像中凸显出来:这是一部以工业空间为背景,以大转型时代为展现对象的独立纪录片。在这部片子里,铁西区的工人们得以通过生活、话语、场景的影像再现,重展那段历史,这是关于一个时代离去时的记忆,一段关于社会时空更迭的理性记忆。《铁西区》由《工厂》《艳粉街》《铁路》三个部分构成,它是一部优秀的独立纪录片,具有史诗般叙事结构的《铁西区》,在中国纪录片史上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此,笔者希望以对《铁西区》的细致解剖为切入口,进入那个时代的历史通道并将隐于影像段落中的时间褶皱逐次展开,释放其中丰富的时光印迹,并凭以书写时代的重要记忆轮廓。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