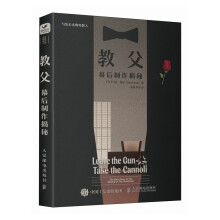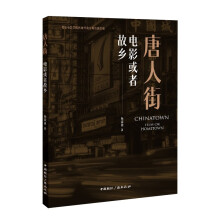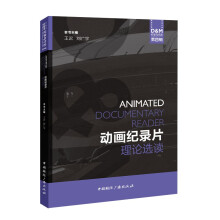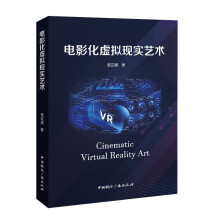从自己的家庭谈起
陈墨(下简称陈):高老师,感谢您接受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咱们从头开始聊,请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高汉(下简称高):1926年1月18号,我生于浙江天台,那是一个山区小县,80%以上是丘陵山岳,耕地很少。我祖父拥有祖上留下来的田产,是个中等地主,他兼做白油生意:从农民手里收购乌桕树籽,制成白色的做蜡烛用的油和可以点灯的燃油。他英年早逝,我没有见过。祖母是乡下一个大地主的长女,身材高大,脚裹得很小,农家一切粗重家务全内行,但目不识丁,生性粗暴,有节俭美德。她生育四个儿子,两个夭折,只剩下我父亲和叔父两人。父亲旧制中学毕业后,在家帮祖母经营家业,叔父在北京上大学。
我外祖父是个秀才,他家是书香门第,拥护康梁维新变法,所以让我母亲从小就进私塾读书,受的都是儒家经典教育,也读诗词歌赋,所以她会作诗、对对子,也爱画画。可是外婆出身豪门,坚守封建传统,一定要为我母亲裹脚。那时母亲还很小,裹脚很痛苦,她就不停地啼哭。外祖父一闻哭声就来剪裹脚布,为此外祖父母之间斗争很激烈。一边是封建传统,一边是维新思想,在对女子缠足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外婆等外公外出,又给母亲裹上脚,这一回用针线把裹脚布缝得严严实实。可怜的母亲年幼无力反抗,只有趴在床上痛哭。外公从外面回家,又听到哭声,又拿剪子去剪。就在这样包了剪、剪了包的反复斗争中,母亲落下了一双不大不小的“解放脚”。后来外公去杭州从事维新活动,北京发生“戊戌政变”,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菜市口遭难。外公因此抑郁愁闷,客死杭州。回家时,只见棺材不见人。我母亲无限伤心,从此失去了支持她的人,只剩下外公为她出嫁准备的一柜子书籍。
母亲来到父亲家,因为两人家庭背景不同,文化差异很大,很难适应。尤其表现在母亲和祖母之间。母亲是大家闺秀,性情温和,擅长书画诗文针黹。祖母是乡下文盲,只知道操持农家事务,节俭发家,性似暴雷,一点就着。母亲只能处处忍让,很难做人。好在不久就分家了,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分成三个小地主家庭。
因为考虑到我们家兄弟姐妹比较多,母亲又坚持子女都要上学,父亲就开了一家百货店,希望从此解决子女学费问题。可是父亲不善此道,来赊账买货的人比欠账还钱的人多。几年下来,资不抵债,难以为继。于是债主盈门,发货人上门要钱的络绎不绝。我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日子,要父亲关店停业,破产偿债。父亲也无良策,就把好田好地拿出来抵债,只给自己留下五亩口粮田和一个小菜园,还有几块无人愿意要的溪滩地——下雨易淹,收成无保证。
我兄弟姐妹六人,我上面有大姐、两个哥哥,下面有弟、妹各一人。我小时候,上学的连我是四个人。学费由母亲典当她的陪嫁物资来解决,有时也当她的首饰。我上初小时,学费没多少。等我上高小五年级那年,出了问题。母亲付了姐姐、哥哥的学费,所余不够一元。我的学费正好要一元。她不得不去找学校的事务主任,要求先让我上学,学费过几天再交。事务主任是我家邻居,说不能开这个头。
她无法可想,看着我发愁。正好这时来了一个住在我家农具仓库里的老雇农,他原是我祖母雇的长工,后来得了疯癫病,不能种田,妻子也跑了,整天东游西逛,到处流浪。那时我家还未破产,父母看他可怜,就让他住在我家农具仓库里,有时也在我家吃饭。后来病好了,他一个人仍住在那里,平时给四邻打零工,有时也帮我们家挑水。他发现我母亲愁眉打结,就问什么事犯难。母亲说差一块钱付我的学费。他一声不吭,从腰包里摸出一块银元,放在桌子上,走了。这样,我才上了高小五年级。
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从此努力考高分。当时制度,每班成绩前三名可免学杂费。我年年是第二名,免费读完高小。
我高小毕业那年,大姐已到杭州省立医专护士学校学习,大哥考进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他们需要的学习费用比过去在本县读初中时增多了,我母亲能典当的东西也已经用尽。二哥响应全民抗日总动员,和同学一起考进中央军校,抗战去了。我该进初中,但是家里确实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父母商量后决定,让我去海游——即今三门县——先当两年学徒再说。父亲说,那里有两家店与我祖上有来往,一家是当铺,一家是咸货行——买卖腌制海产品的,让我选一家。我无可奈何,选了当铺。我只能眼看着同学们备课考初中,自己已无缘继续升学。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救星,是我的二舅公,我母亲的二舅舅。他是当地一个大绅士,曾在日本留学,加入过同盟会,当过省议员。他经常来我们家,看我的作文,觉得我的作文很好。他问我,考中学你准备得怎么样了?父母就跟他说了不升学的打算。二舅公拍着桌子大怒,说你们真是糊涂,这个孩子怎能不升学?!当什么学徒?!当时他说,今年县政府在初中班设立公费生,差不多每班有一个,五十个人中有一个,原来是没有这个制度的。他说你们让他去考,如果考取公费,就可以公费上学,一个学期还有四块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