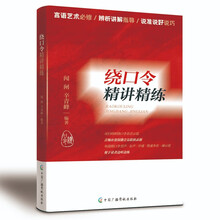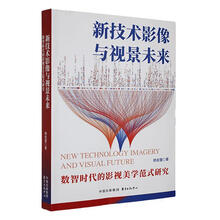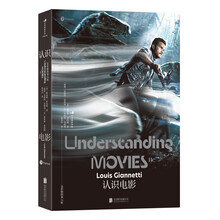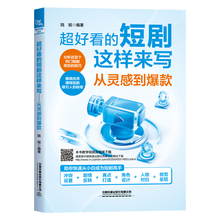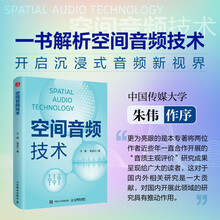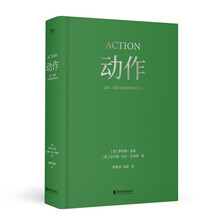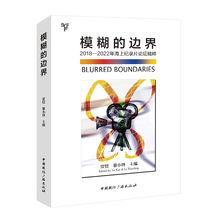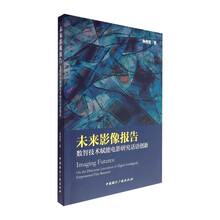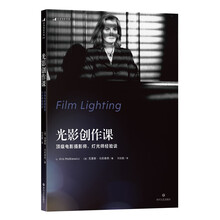《中亚五国电影发展历程》:
《养子》中少年与父亲的冷淡和冲突,再一次延续到了下一部青少年题材的电影《猩猩仔十七岁》中。猩猩仔的父亲是一个老酒鬼,整天和几个落魄的中年人喝酒赌博。猩猩仔只能从窗户和镜子远远地看着父亲。其中有一个镜头通过结网的蜘蛛转移调焦到沉默愁苦的父亲,在母亲喋喋不休的辱骂声中黯然神伤。当母亲终于离去,在墙上的相框里迅速闪过了一个苏联军人英姿焕发的一生。父亲在破碎的镜子里凝望自己,头顶的墙上挂着骄傲的军功章,可他已经失去了属于他的年代。父亲至死不改的堕落和绝望,虽生犹死。猩猩仔只能离开空荡荡的家加入了迷狂的派对,他急于和维嘉表白似乎是要在一夜之间就顶天立地,长大成人。而实际上,他和沙西躺在天桥上的时候,还不知道维嘉是什么人,爱情又是什么?!猩猩仔远赴兵营的绿皮火车在抽查违规抽烟的紧张气氛中离去,父亲依然缺席,母亲已身在远方,没有人来送行。只有火车烟雾中作为“成人试验”吻过的疤脸女同事,茫然地指挥火车远去。电影结尾墙壁上一幅又一幅童年刻画的抽象图案,昭示着青春的各种符码——扭曲,夸张,惶惑还有恐惧,幻想。
《空房》是一部关于吉尔吉斯少女的故事。电影中17岁的女孩阿萨为了在经济上帮助酒鬼的父亲和几个弟弟,必须通过嫁给村里离异的富豪,以承担长女和死去母亲的责任。阿萨本想和男友私奔,但是不想男友也是同样的自私怯懦。对于故乡万念俱灰的阿萨只能逃离故乡,去莫斯科,巴黎——在幻想中去寻找她内心憧憬的生活。无论是在莫斯科举目无亲,还是遭遇老乡出卖,被前夫和前男友追杀,她都没有走回头路。阿萨的最后一站是巴黎,只可惜她连去巴黎的方式都不知道,就在盲目的拦车搭车中被刺伤。躺在血泊中的阿萨卖掉了孩子,也失去了金钱,更断送了去巴黎的“好生活”。电影结尾阿萨又回到了吉尔吉斯一个草台班子的舞台,做着自己向往的歌手。她蹩脚的演唱已经预示了此路又将是颠簸坎坷,但她的勇敢坚毅却又透出一种西西弗斯般的后现代诗意。
如果说上述几部影片是通过对于苏联作为民族身份隐喻的少年和女性的解构,来表达面对逝去的乌托邦一代人复杂的心境,那么《极光》这部影片则是对于吉尔吉斯当代民族身份建构的彻底否定。影片中苏联时代建设的疗养院极光到了独立时期,依然保存着艾特玛托夫《白轮船》的美丽造型,并且保持着苏联时代的一切基础设施。但随着政治的腐败和政局的动荡,经济危机和广泛的贫困,极光由于经营困难而被邻国中国租用改造经营20年。极光在无限的惆怅中被移交之际,却早已失去了往日苏联时代的浪漫诗情,反倒是吉尔吉斯当代混乱格局的缩影。前来怀旧的老电视节目主持人因为无法容忍当代青年的粗暴流氓举动,开枪打死了胆大妄为的黑社会青年。而黑社会青年的母亲是主持人的粉丝,父亲是他的同学,在郁金香革命中死去。前来谈生意的落寞中年女商人因为客人失约,误入了黑帮青年布设的猥亵陷阱。她的苹果手机里的开机视频揭露了极光疗养院压榨员工的残忍事实,而猥亵她的男人也误被手机录下了虐恋疯狂的暴力举动,并在和中国生意人的纠纷中不知所终。剩下的住客,堂而皇之地吸毒,高雅地乱伦。为了赚取中国生意人的租金,极光老板自以为掩盖了所有的罪恶,但新的罪恶依然渗透在极光的每一个角落,表明该国在独立后更加边缘漂泊的身份困境。
这几部后苏联的吉尔吉斯艺术电影,都表达了旧的乌托邦崩塌之后,中亚所面对的失序的社会和失序的人生。他们对逝去的理想主义时代充满怀念,也对独立后的现状和未来感到绝望,尚未找到新的身份认同和归属。这是中亚五国独立后面对艰难的国家建构和民族身份塑造的普遍心境。
7.4.3.2当代民族身份的探寻
与库尔曼江·达特卡这样的国家神话中的民族英雄相比,处于边缘的精英知识分子塑造了反观“母体”的反叛英雄。他们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从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中为劳苦大众盗取光明,维护逝去的古老传统,探寻着当代吉尔吉斯独立的主体身份。雅坦·阿迪卡可夫的《盗光者》(The Light Thief,2010)和《半人马》(Centaur,2017)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盗光者》和《半人马》都是关于“小偷”的故事,通过他们表面违背道德的“偷盗”行为,表现了在全球化格局中践行民主制,与各个超级大国商贸合作,不仅没有使吉尔吉斯普通人更加富裕,反而使这个国家在不同文化的侵袭下逐渐失去了古老的传统和信仰。《盗光者》中年过半百,满脸皱纹的电工,却有一个富有象征性和诗意的名字——“光先生”,而这个小村庄也不无梦幻地被叫作“风吹谷”。影片中的投机政客贝克扎克购买了风吹谷的土地,通过向中国,俄罗斯还有美国等大国招商引资,控制了当地的话语权。所有违背他的人,包括村长和文化部长在内都将被杀人灭口。光先生是带来光明的电工,帮助穷人偷电。同时他又是一个关于“光”的工程师和梦想家。他在自己家里做了一个很大的风车,梦想着在山谷里建很多的风车,利用山村处在风口的地理位置为全村人免费发电。他为了黑喑中的光抵抗到底,结束了焦灼而无力的一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