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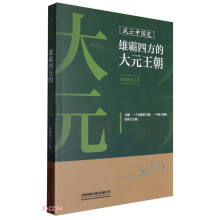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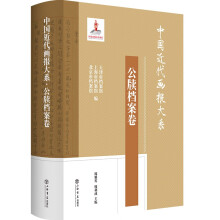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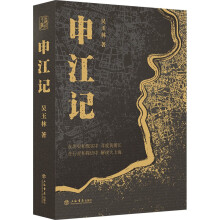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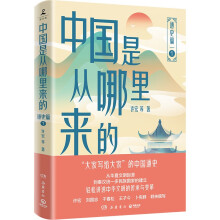
集体化时期的档案资料,能够被发掘出来,难能可贵。这批资料是关于集体化时代基层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变迁和普通民众个体人生的系统记录和全方位呈现。这些丰富的材料既关涉宏观、中观层面又连接微观,不仅体现出党和国家自上而下对于村庄和农民个人社会管理的路径、方式和逻辑,而且也从村庄自身运作和个人的内在视角呈现出集体化时代的历史演变及其折射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斑驳陆离,这在以往的历史资料中并不多见。当然,这些资料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烙印,反映出了集体化时代独有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
该套资料对学术界相关问题的纵深研究大有裨益,对我国当今振兴农村、妥善解决农村问题有非常深远的借鉴价值。
经过长时期的准备和努力,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选编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丛编》(以下简称《丛编》)就要付梓印行了。我受中心诸位的委托,现就相关问题做一点说明,权且作为《丛编》的一个序言。
一
何谓“集体化时代”?“我们认为,集体化时代是指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结束的时代。此间约四十年时间(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前后相继,一路走来。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农民走向集体化,实践集体化的时代,也是中国农村经历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结束于改革开放后普遍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下限大概没有什么分歧。对其上限的界定那就见仁见智了。陋见所知,或曰“合作化时代”,或曰“公社化时代”,还有以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为起点的诸多看法。我们以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根据地普遍建立的互助组应该是中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的起点。这是因为,互助组的目标就是集体化。早在1943年11月底,在各根据地普遍建立各类互助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明确指出,几千年来的个体经济,使农民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我们不能因为互助组仍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就把它和后来的初级社、高级社割裂开来,更不能以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为界将集体化时代拦腰截开。正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基本单位,也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互助组之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从事生产生活,互助组开始由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走向集体生产;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以“社”为单位,虽有“半社会主义”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之别,也有“大社”与“小社”之别,但“社”作为基层单位是不变的;人民公社时期的“社”与初级社、高级社时期的“社”有了本质的不同,人民公社已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乡”,甚至出现了联村社、联乡社。到1962年《农业六十条》通过后,公社、大队的规模开始缩小,基本的核算单位由原来的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就是现在的“村”,生产小队也就是一个生产小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迄今收藏的近300个村庄集体化时代档案中不仅有大量村级的,更有大量生产小队的档案,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二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来重视民间文献资料的搜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相关的研究人员已经在史料收集上将眼光投向基层社会。我在业师乔志强先生的安排下,抄录收集了刘大鹏《乙未公车日记》和《桥梓公车日记》,加上先前先生摘抄的刘大鹏《潜园琐记》,以及之后众多学生几年间才抄录完毕的《退想斋日记》中的“有关社会史资料”,为中心收集地方文献建立了初步的价值取向。在此之后,我们一直关注着社会史研究资料的收集,水利、晋商、灾荒、秧歌、贱民等方面的资料,成为中心的特色收藏。
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引起我们的注意,经历了一个思考和实践的过程。最初我们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将目光和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的文书、碑刻等资料上,而对现当代的村庄档案关注不多。2003年冬天,我在太原市南宫旧书市场发现并收购第一批清徐县高白公社东于大队有关档案后 ,有关的思考和实践就未曾间断。
经过个人将近一年时间的田野考察和诸多准备,2004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在山西大学文科楼大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走向田野与社会---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的学术报告,明确界定所谓的“集体化时代”,呼吁以社会科学工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抢救、搜集现存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
需要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是,1949年—1979年这样一个相对我们较近的历史时期,散落在广大农村社会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文献也在快速地流失和消失过程当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发展速度加快,走进田野和农村,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新中国成立以前,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旧房舍迅速地被新一代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建筑所替代,有的富裕农民二十几年来甚至搬迁了两次、三次(乡镇政府,大队、村委会也是如此)。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旧的农民住宅,甚至在相对偏僻的地区还可以看到个别古村落,但那毕竟属于少数。很可能,当你走进这些旧的农民住宅和古村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已是“人去楼空”,甚或“人去村空”,他们已经连人带物搬迁别处,留下的只是闲置的、有些可能是作为旅游开发的景物。可怕的是,每一次的搬迁总伴随着一次物什更替,同时也是一次文献资料的散失,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地方文献在农民搬迁过程中不经意地不知流向何方,一些汇聚到了废品收购站和造纸厂。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甚为痛心和遗憾的事情。只要我们具有“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关怀,只要我们具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良知,就有可能在这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十余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全体师生,不避寒暑,栉风沐雨,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广泛搜集散落在全省各地农村的档案,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知道,至今仍然存有档案资料的村庄,往往位于较为偏僻的地区,路途较远,交通又不便。前往这些地方需要大费周折,而又时常是一无所获。资料本身不易遇到,而获取这些资料则更加困难。一些村民对我们的工作缺乏了解,甚至多少存在疑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便住到村庄里,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是在抢救历史文化资源,是为了从事学术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保存档案,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和他们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另外,我们还会请有关的村民到中心来进行参观和座谈,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已收集到的档案整理保存的状态,和他们签署有关档案保存和使用的协议。这一过程虽然艰辛而烦琐,但也经常让人感到欣喜和振奋。一个村庄濒临毁灭的档案资料的发现,一个资料研读中获得的新认识,一位亲身经历而又倾力相助的热心人,都会使我们感受到那份只有置身其中才能获得的充实与快乐。
最初,我们的档案收集工作是“从家乡做起”的。我和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山西农村,农村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通过这些地缘关系,不仅可以了解档案存失的真实情况,而且容易沟通和交流,绝大多数同学都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也有不小的收获。近年来,这类档案资料的收集越来越难,或许是村民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也在注意保护和整理这些资料,这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或许是因为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学界的朋友,甚至收藏者也在有意收集此类资料。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如今去太原南宫市场“购买”农村档案,不仅很难见到,价位也是高得出奇。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已将“从家乡做起”与“集体调查”结合起来。事实上,此种“集体调查”的做法在中西方史学实践中已有先例可循。以“史学即史料学”一语闻名的傅斯年在其民国时期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主张“集众式的研究”,以集体的力量搜寻新史料在当时成了一种口号,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自觉,而非个人的嗜好。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同样将“集体调查”作为他们重要的研究方法。J. 勒高夫在谈到吕西安•费弗尔《为史学而战》一书时说,费弗尔在书中提倡“指导性的史学”:它是指以集体调查为基础来研究历史,这一方向被费弗尔认为是“史学的前途”。对此,《年鉴》杂志一开始就做出榜样:它进行了对土地册、小块田地表格、农业技术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贵族等的集体调查,这是一条可以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途径。自1948年创立起,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的历史研究中心正是沿着这一途径从事研究工作的。
最近这些年,我们利用寒暑假组织中心师生对昔阳、潞城、永济、浮山、绛县等地进行了“地毯式”的“集体调查”,有了可喜的收获。“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于此潮流,谓之预流。”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话不断回响在我们耳畔,也在不断催促着我们前行。
资料的搜集仅仅是工作的第一步,收藏并非目的,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如何使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能够为学界所利用是从事此项工作一开始便有的追求。对收集到的档案资料进行细致整理是档案运到中心后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资料的整理是中心每个师生的必修课。基本的做法是:第一步对档案进行分类,以村落为单位,将收集到的档案按照年份的先后顺序,以上级来文,地方文件,账册,“四清”档案,人口、家庭、婚姻档案,工作笔记,学习资料,个人材料等在保存档案原始样貌的基础上进行细致分类,以便下一步细致地整理录入。第二步是档案编排目录工作,即根据第一步整理分好类的资料,一张张录入到电脑中,建成电子文档,同时对每份档案进行编码,一个编码对应一份档案,并对每份档案重新装袋,这样更便于检索和保存;第二步工作完成后的成果,就是每一个村庄都有了一份简要的对应目录。第三步是装柜,按照第二步整理而成的目录,以档案袋为单位,装入档案柜中,保存档案。
同时,随着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持续深入,我们开始运用现代技术收集口述资料,档案资料的电子化、数据化方面的工作也在不断尝试,我们建立的“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档案数据库”,在网上已经逐步开放。在整理过程中,对于档案资料的修复与保存是另一项重要工作。每一份搜集到的档案资料都是它所处时代的历史呈现,都需要进行妥善地处理与保管。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一些档案资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潮湿和虫鼠的破坏。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资料整理修复工作室,购置了先进的处理设备,全面细致地对这些档案资料进行铺平、熨烫、复原和扫描。同时,我们建立了恒温恒湿的资料保管室,以免这些档案资料受到进一步损坏。
为做好这些工作,中心师生投入了大量心血。每年寒暑假,在田野调查与休息之余,师生们便聚集在中心的工作室,进行资料整理与编目工作。几张书桌拼接起来便是简易工作台,常常是十几台机器同时运转,一干就是一整天。为防止灰尘与病毒,家用围裙、医用手套与口罩成为简易的“防护服”。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常常令人欣慰和感动。我经常讲,史料整理爬梳是史学的基本功夫,档案的整理过程其实也是对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研究和利用的过程,师生在其间接触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有了熟悉材料、提出疑惑和解决问题的机会。许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即是通过这样的实践获得了灵感与思路,中心教师的一些研究成果事实上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与萌发的。这也是我们多年从事社会史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努力与收获。
2011年和2013年我们相继出版了《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和《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两部著作,利用中心所藏档案,初步展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的面貌。这些成果的出版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受到了学界前辈的肯定与鼓励。以这些档案资料为基础,我们申请了多项科研项目:2008年,由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获准立项;2012年,由我牵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获批。其他研究人员申请的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亦有多项。同时,一些国内外学者、学术机构与我们的合作也逐步开展,以期共同推进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研究。2007年,我们和日本学者合作的国际项目“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研究— 道备计划”,便是以平遥县道备村的集体化时代档案为主体展开,每年与包括日本宇都宫大学的内山雅生教授在内的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联合在山西四个村庄进行持续调査。2013年,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李伯重教授来访中心并商讨合作事宜,探讨中心集体化时代档案资料的数字化问题,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集体化时代“四清”档案数据库。这些合作研究,既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也让我们认识到了集体化时代档案资料建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三
迄今为止,我们进行田野资料采集的分布点已经从南到北遍布整个山西省,收集并整理的档案资料涉及山西南北近300多个村庄或单位,总计在数千万件。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各方人士除了对我们工作的肯定甚至赞叹之外,也有人不时地追问,我们是怎样收集到如此庞大的档案资料。对此,我在一个学术座谈会上这样讲过:“这批农村基层档案的发现、搜集、整理,并不是用钱买来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不是用钱买来的,而是靠师生长年累月辛勤的工作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换来的;是我们自己称之为的‘集体调查’,而不是个人的零散行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心血来潮的盲目行为。”“我们并不是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更不是将其视为‘红色文物’期望它增值,实在是想为中国历史及其研究留下点东西,尽一份当代学人的社会责任。”
大体而言,迄今我们搜集到的档案基本以村庄为主,还有一些为公社、灌区、供销合作社、百货公司、工厂等单位的文本资料和实物。从生成时间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资料,各地或由于县、省级档案馆出于对档案资料的统一管理已经收回,或由于其他原因,村庄档案已经少有留存。个别地方明清以来的契约、文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村庄档案有少量收藏,例如有关太行根据地李顺达互助组、医疗卫生、灭蝗运动的档案资料,侯马市张王大队1945—1949年关于解放战争对村庄的影响和村庄战时负担的档案等,但中心大量保存的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82 年人民公社解体这一时段的档案资料。从具体内容来看,各个地区和村庄都有自身的体系和特点,或以个人档案突出,或以成册上级档案突出,或以较为完整的账册突出,或以极为详细的各种经济活动的分类统计数字突出。
整体上看,目前中心所藏档案资料可分为八个大类,分别为支部群团文件、行政文件、上级文件、科技档案、个人档案、财务档案、历史档案、内部资料以及其他类型的档案资料。具体情况如下:
支部群团文件
农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最基层组织,是村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围绕这一核心,各种群团组织同样在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心现在收藏的这部分档案资料包括村庄党支部会议记录,综合性工作的文件,支部关于组织工作的文件(包括各种名册),支部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支部关于治保工作的文件,支部和驻村工作队关于一些运动的文件和专案材料,支部的请示和上级党委的批复、批示,等等。关于村庄的其他群团组织的资料,主要有村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的文件和有关材料以及村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事迹材料。通过这些档案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村庄党群组织的人员构成、各项工作安排以及日常运行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此外,一些村庄还保留了由村庄党支部组织编写的村史、家史、专题材料及村庄大事记、历史沿革等历史材料。这些历史资料虽然因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存在失真的情况,但仍然能够呈现出村庄或者个人家庭的历史发展过程。
行政文件
村庄基层行政组织形成的各项记录构成村庄档案的另一大类。这部分档案主要记录了村庄各项公共事务的情况,包括村庄会议记录、各种文件、户口登记册和迁移证、土地证、房产证、林权证和交接凭证的存根,以及村庄企业、科研、基建技术档案,村庄与有关单位的来往文书、合同、协议书,还有村庄的请示与上级的批复、批示,等等。
上级文件
上级政府下发文件是上级传达和执行各项政策的工具,也是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这些文件多是带有指导和指示性的计划、决定、意见及通知,分别来自党政系统的不同层级,既有专门针对某一村庄的文件,又有下发的全国性文件。其中包括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及各部门针对该村庄的文件,国务院、省、地、县、公社及各部门针对该村庄的文件,县委、公社党委及各部门的一般来文,县政府、公社及各部门的一般来文,中央、省委、地委及各部门一般来文,国务院、省政府、行署及各部门一般来文。
科技档案
科技档案是农村档案中出现较晚的一类档案,直到1980年山西省委办公厅发布的《生产大队档案管理办法》实施后,山西农村档案体系中才出现了“科技档案”。中心收藏档案中,涉及农业生产科技内容的档案资料较为丰富,主要包括生产大队改良土壤、水利建设、培植优良品种以及农业基本建设等有关科研方面的文件材料。
个人档案
个人档案在多数村庄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个人档案包括村庄党团员个人档案,村庄干部个人档案,这两类个人档案主要是“四清”运动中对农村党员干部“四不清”行为的审查鉴定,干部对自身经济问题的自我检讨和政治立场的个人鉴定,他人对于干部个人如记工分问题、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问题等的检举揭发和证明材料,其中主要涉及干部对于粮食和金钱的贪污。村庄
“五类分子”个人档案、村庄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人员个人档案,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投机倒把、偷盗赌博以及参加过旧政权等组织的一般人员的个人档案。
财务档案
财务档案主要是涉及村庄各种财务活动的记录,是中心所藏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中数量最为庞大、体系最为完备的一类资料。其中主要包括村庄的财务统计、年报和决算表、财务账册、大小队的票据单据,等等。其中财务账册尤为丰富,包括总账、分类账、分户账、日记账、工分账、社员往来账、实物收付账、现金收付账、实物明细账、各项收支账、粮食账、固定财产登记账、一般财产登记簿、无价证券登记簿等,涉及村民生活的各方面。这些账册资料作为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乡民日常经济生活的反映,是村庄档案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历史档案
这部分档案资料年代久远,保存数量相对较少,包括村庄在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革命历史文件或旧政权文件等。还有一些村庄保存有民国以前的契约、地亩册等资料。这些资料在过去一般保存在个人手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或被没收或被查抄,为村庄集体保管。
内部资料
这部分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反映村庄活动情况的文章、照片,村庄编订的各类专题文件汇集,记载本村庄活动的书刊、杂志,村庄内部学习资料,村庄主要领导人的工作笔记,等等。
总之,目前中心收藏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可谓“无所不包,无奇不有”,能从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反映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历史面貌。上述所举仅为其大要者。事实上,中心现在所藏的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是一个庞大的“资料群”,同一村庄或同一县域内的不同档案资料之间相互关联,存在着一种人际关系上和区域范围上的内在关系。我们期望,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会建设成为一个集体化时代的资料收集中心和研究中心。
为了使学生和各界人士对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和理解,2008年,我们特意建设了一个占地 400余平方米,集档案、图片和实物为一体的“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览馆”,各界反响十分热烈,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2012年,该展览馆被确定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也是中心所藏资料另一种形式的展现。
四
近年来,一些学术机构或个人已经整理出版了类似的档案。例如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开展的关于联名村档案资料的整理与网络资源的建设,南开大学张思教授整理的《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编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广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编的《一个村庄的原始记录:广东顺德县北水村经济社会史料选编(1950—1983)》等,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的断层。但也可以发现,这些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各有侧重和特色。与上述出版物不同,我们按照中心所藏档案资料的特征,决定以“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丛编”命名出版。
《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丛编》,按照以下原则编辑出版:
1. 以村庄为单位全部影印。我们知道,集体化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些农村档案资料也被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原始资料上的一些细节,例如资料上的印章、“最高指示”、涂抹修改的痕迹、当地方言的书面表述方式,甚至记录载体不同质地和记录人员字体都是反映当时农村社会真实历史面貌的重要内容。文本本身即是一种历史存在。因此,我们不再对这些资料进行重新编辑,而是采用全部影印的方式进行出版。我们相信,这种出版方式更能原汁原味地体现这批档案资料原有的历史面貌,也更有利于学界使用与研究。
2. 尽量保持原始形态。在整理的编排顺序上,我们以遵照村庄档案原始保存顺序为原则。一些村庄档案资料保存情况较好,多为已经整理好的装订成册的档案资料。我们认为,村庄原始保存体系事实上反映了当地对档案的认识,也是基层档案资料原始面貌的一部分。如果以“后见之明”进行编排,很可能打乱这些档案资料的原本体系与内在脉络。因此,对于这部分村庄档案,我们按照其原有体系进行编排。而另外一些村庄的档案资料实际上已经濒临毁灭,村庄也未对其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在我们发现之际基本上处于散漫无序的状态,不能自成体系。对于这部分村庄的档案,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按照不同的类别和年份进行重新编排,以便读者查阅。我们力图最大限度地体现村庄档案资料的原始面貌,以最大限度地方便研究与利用。
3. 实行分辑主编制。《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丛编》主编由行龙担任,分辑主编则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各位教师担任。原则上以村为单位分辑出版,或两个、三个村庄合辑出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不断地将此工作继续下去。
希望这批农村档案资料的陆续出版,能够为目前蓬勃发展的集体化时代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一学术新领域。我们愿与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行龙
2022年4月11日
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第1册
青介山村农业税分户清查(1952年)
杨塔村农业税分户清查(1952年)
侯官屯村农业税分户清查(1952年)
上吾其村农业税分户清查(1952年)
下吾其村农业税分户清查(1952—1953年)
第2册
燕窝村农业税分户清查(1952年)
上吾其村农业税分户清查(1953年)
后营村农业税基础数字统计表(1953年)
下吾其村农业税分户清查(1953年)
上吾其村农业生产计划(1956年)
上吾其乡基层选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登记表(1956—1958年)
中共上吾其乡党委机关党员花名册(1957年)
上吾其乡农业税数字(1957年)
团省委、县委、县妇联意见(1962年)
第3册
各大队团员志愿书登记(1950—1965年)
各大队团员志愿书(1965年)
第4册
各大队团员志愿书(1965年)
关于四清运动各种情况统计及经济问题落实统计表(1964—1965年)
第5册
关于四清运动工作总结、报告及各大队的村史、家史等(1965—1966年) 上吾其公社固定物资清点、财务移交及发展规划(1963—1965年)
上吾其公社党团组织关系介绍、通知(1961—1966年)
本社各大队破旧立新没收物资情况统计表(1966—1967年)
上吾其公社办理迁移证存根(1964—1968年)
第6册
上吾其公社迁移证登记(1965—1969年)
上吾其公社团员志愿书(1965—1969年)
第7册
上吾其公社农业税变动申请、通知(1966—1971年)
上吾其公社迁移证存根(1969—1972年)
上吾其公社迁移证登记(1969—1976年)
第8册
上吾其公社经济退赔统计表(1972—1973年)
上吾其公社各种记载登记簿(1965—1967年)
上吾其公社审批新党员通知(1965—1974年)
第9册
上吾其公社迁移证存根(1973—1976年)
上吾其公社关于调干介绍及通知(1966—1976年)
上吾其公社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1962—1976年)
上吾其公社干部任免决定及通知(1966—1976年)
上吾其公社各大队组织花名登记(1966—1976年)
第10册
上吾其公社党员统计花名表(1964—1977年)
上吾其乡民兵登记表(1956年)
上吾其乡生产规划和劳力调整表等(1956—1958年)
上吾其乡选举材料(1956—1957年)
上吾其乡社员收入对比表(1958年)
第11册
上吾其乡兵役登记册(1958年)
上吾其乡各村户口登记册(1958年)
第12册
上吾其乡各村户口册(1958年)
上吾其公社监委会、团委、武装、妇联花名统计表等(1962—1963年)
上吾其公社武装部民兵花名登记册等(1963年)
上吾其公社电话记录、请示(1963—1964年)
第13册
上吾其公社各种统计报表(1958—1964年)
上吾其公社电话会议记录簿(1964—1965年)
上吾其公社民兵、共青团、妇联花名册(1964—1965年)
上吾其公社武装部民兵花名册(1964—1965年)
第14册
上吾其公社电话记录簿(1965—1966年)
上吾其公社团员、妇女花名册(1964—1965年)
上吾其公社各种情况报表及会议记录(1965—1966年)
第15册
中共中央、省委、地委四清办公室、组织部、农村政治部通知、报告、通报
(1965—1967年)
阳高县人委、农村政治部通知、报告、意见、总结(1966年)
上吾其公社教师政审登记表(1966年)
阳高县人委会、革委会核心小组及各部门通知、决定、规定、纪要(1967年)
第16册
阳高县核心小组、革委、财贸部通知、通报、决定、意见、报告(1967—
1968年)
阳高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通知、意见(1969年)
上吾其公社外调介绍信、介绍信存根、工资调整存根及申请(1968—1976年)
上吾其公社团员介绍信及存根(1962—1970年)
阳高县革委、人武部、核心小组、政工组、生产组通知、意见、规划、报告
(1970年)
第17册
阳高县三养排队表及农机、计委规划表(1977—1978年)
上吾其公社优抚救济统计表(1963—1971年)
上吾其公社各种记录簿(1970—1972年)
第18册
上吾其公社结婚申请书登记(1965—1972年)
第19册
中共阳高县委、县革委、人武部、生产组决定、安排、意见、通知(1971年)
上吾其公社各种记录和统计表(1972年)
第20册
县委、革委、人武部、政工组、生产组、工业局、粮食局通知、通报、意见、
安排(1971—1972年)
上吾其公社电话、汇报记录,生产情况、计划报表(1972—1973年)
第21册
阳高县委、革委、各部门通知、报告、意见、通报(1973年)
第22册
上吾其公社电话会议、工作记录及统计报表(1973—1975年)
上吾其公社各种记录簿(1975—1976年)
第23册
上吾其公社各种记录簿(1973—1975年)
上吾其公社办理结婚申请书登记(1973—1975年)
第24册
上吾其公社办理结婚申请登记书(1972—1977年)
上吾其公社发放布票登记(1974—1975年)
上吾其公社收党费存根(1965—1977年)
第25册
上吾其公社档案移交及文件清退登记(1965—1972年)
上吾其公社生产进度统计(1975—1976年)
上吾其公社各种情况记录簿(1976年)
第26册
上吾其公社各种记录簿(1976—1977年)
中共阳高县委、县革委报告、通知、决定、规定、意见(1976年)
上吾其公社结婚申请、介绍信、领取生死布票、党员迁出迁入介绍信、人员
调出调入介绍信(1966—1977年)
上吾其公社迁来迁移证、准迁证存根、开出迁移存根(1975—1977年)
第27册
阳高县革委电话指示、生产进度统计表(1968—1969年)
中央阳高县委、县革委通知、报告、通报(1974年)
阳高县文教组、计委、民办、财办等各部门通知、报告、意见(1974年)
第28册
上吾其公社发放布票存根(1973—1974年)
中央阳高县委、县革委、县委办公室、县财贸组通知、意见(1975年)
第29册
阳高县农办、计委、办事组、水利局、农林局、农业局各部门通知(1975年)
上吾其公社各大队干部花名及各类组织情况统计(1965—1976年)
上吾其公社发放布票登记(1975—1976年)
第30册
上吾其公社会议记录、电话会议记录(1977年)
上吾其公社简介、各种报表(1980年)
各队组织花名表、生产进度、请示报告、调资表,模范党员、先进党支部表
(1974—1977年)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