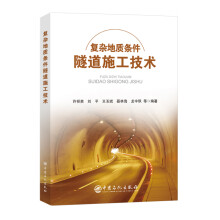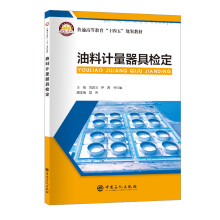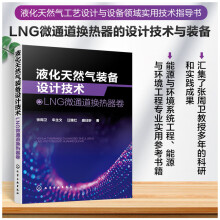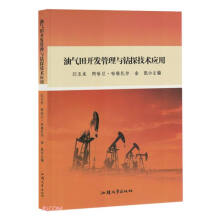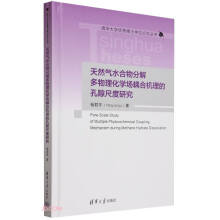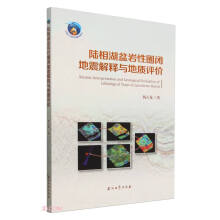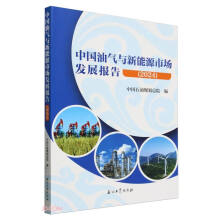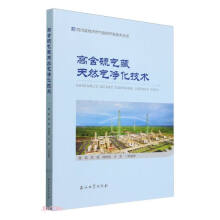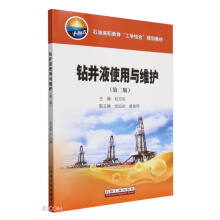第1章盆地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研究现状与前沿问题
储层是油气勘探的直接目的层,从理论方面考虑,油气勘探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储层的认知。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面临诸多理论和技术问题,而储层问题不仅首当其冲,且*为直接。
1.1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产出的基本特征
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产出的*基本特征包括其发育的盆地类型、地层时代、岩石类型、储集类型等方面。
1.1.1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的基本定义
对于含油气盆地而言,广义的储层是指具备一定储集空间的岩层,而狭义的储层是指具备一定量级烃类储集空间且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岩层。从油气地质学角度,储层类型可以有多种划分原则,包括储集物性、储集组构、岩石类型、产出深度、储层成因等。
从岩石类型看,沉积岩、火成岩和变质岩三大岩类都可以作为储层,但以沉积岩为主。从埋藏深度看,储层可以发育在从地表到浅层、中深层、深层、超深层的广大范围,但储集性差异显著(参见图1-1)。当今油气勘探已经进入深层-超深层时代。
目前有关含油气盆地“深层”的概念基本是以深度标定的。一方面这是对油气勘探成本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间接或粗略反映了地下温度、压力、流体环境的变化,这对于勘探规范和勘探家来说无可非议。按照行业规范,在我国中西部地温梯度较低的油气盆地中,深层对应深度为4500~6000m,超深层对应深度为大于6000m;而在地温梯度较高的东部油气盆地中,深层对应深度为3500~4500m,超深层对应深度为大于4500m。
鉴于盆地热流和地温梯度差别较大,上述两方案是比较笼统的。根据全球盆地热流及相关研究(图1-2),建议使用三档划分深层和超深层,即低、中、高地温盆地的深度标定体系(表1-1)。事实上,同一个盆地不同二级构造单元、不同深度的地温梯度也存在明显差别,尤其是伸展型盆地,因此表1-1的划分仍然是框架性的。
显然,盆地“深层-超深层”的概念应该是动态的,是随着探测技术发展和认知程度加深而更变的。因为油气勘探的认识下限在不断下延、拓展,根据地球物理探测资料,相当一部分沉积盆地的现存*大埋藏深度可以超过12000m,乃至18000m,深层勘探领域前景仍然广阔。
参考油气勘探中常用的深度及相关盆地的大量温压背景资料,表明狭义的深层地温多大于120°C,静岩压力大于90MPa;狭义的超深层地温一般大于160°C(可达300°C),静岩压力大于120MPa(可达280MPa);地层流体压力虽然变化较大,但由于深层流体对静岩压力的(部分)承载,因而可达50~100MPa,甚至更高。从地质条件特别是对岩浆-变质作用条件分析,盆地深层“高温-高压”条件并不值得惊奇,但对于大多在表生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沉积岩石学而言,上述温压条件下的流体-岩石作用机制我们确实知之甚少。
1.1.2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产出的盆地类型和地层时代
统计表明(Evenick,2021),全球*具油气勘探潜力的盆地,其对应充填厚度一般较大,这些盆地类型主要为被动陆缘、前陆/前陆冲断带,挠曲和冲断带、克拉通(叠合)(参见图1-3),而这几类盆地也恰恰是目前认知的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产出的主要盆地类型(表1-2)。当然,裂谷/裂陷、走滑等盆地也有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产出。
总体上看,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产出的盆地类型和地层时代具有如下特征。
(1)新元古界等古老层系的深层-超深层储层,主要产出于克拉通(叠合)盆地中,极少见产出于前陆盆地、裂谷/裂陷盆地、走滑盆地、被动陆缘盆地。
(2)古生界深层-超深层储层,主要产出于克拉通(叠合)盆地及前陆盆地中,极少见产出于裂谷/裂陷盆地、走滑盆地、被动陆缘盆地。
(3)中-新生代的深层-超深层储层,主要产出于前陆冲断带、被动陆缘,以及裂谷/裂陷和走滑盆地,极少见产出于克拉通(叠合)盆地。
1.1.3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的岩石和储集空间基本结构类型
碳酸盐岩、碎屑岩是深层-超深层油气储层的主要岩石类型(大类),但实际组构或成因类型要复杂得多。对全球储集空间类型的半定量统计表明,碳酸盐岩孔、洞、缝等多介质储集结构类型发育,而碎屑岩(砂岩为主)相对单一(图1-4)。
相比较中浅层,深层-超深层储集空间结构类型存在特殊性。总体上,随深度增大,大孔、洞呈现明显衰减,而与裂缝(含扩溶)有关的储集结构类型增多,尤以岩溶型碳酸盐岩*为典型[图1-4(a)]。非岩溶型碳酸盐岩储层的储集结构类型相对单一,其深埋演化与砂岩类似,只是在成因上次生溶蚀孔、裂缝及扩容孔隙的占比可能略高[参见图1-4(b)],其压溶-蠕变相关的成岩产物丰度较高。
虽然大多数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始终以粒间孔为主,但与裂缝(含扩溶)有关的储集结构类型显然不容小覷[图1-4(b)],尤其在超深层,这类储集结构类型对岩石渗透性的作用至关重要。需要说明的是,图1-4给出的孔隙相对丰度是一个半定量的、综合性的岩石大类评估,不针对特定地区的储层岩石类型(亚类或种类)。
对于不同时代的盆地而言,深层-超深层储层产出的岩石和储集空间基本类型具有如下特征。
(1)新元古代等古老层系的深层-超深层储层,以碳酸盐岩为主,孔、洞、缝多介质储集类型组合发育,极少见碎屑岩类型。
(2)古生代的深层-超深层储层,碳酸盐岩、碎屑岩(砂岩为主)兼有,前者多介质储集类型组合发育;但碎屑岩主要产出于克拉通(叠合)盆地及前陆盆地中,孔隙型储集盆地深层-超深层沉积成岩作用与油气储层形成分布类型发育。
(3)中-新生代(特别是晚中生代一新生代)的深层-超深层储层,碳酸盐岩、碎屑岩(砂岩为主)兼有,前者多介质储集类型组合发育,局部克拉通、伸展盆地中可发育孔隙型储集类型;但前陆冲断带、裂谷/裂陷以及走滑盆地的深层-超深层多以碎屑岩储层居多,缝孔型、孔隙型储集类型发育。
1.2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研究概况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上深层油气探井主要分布于北美、墨西哥湾、东欧、西伯利亚等油气区(MaKCHMOBhap.,1984),除墨西哥湾外大多位于稳定克拉通区,其深层大致以4000m为界限。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深层油气探井逐步向大陆边缘和深水区发展,而相应的深层油气集中-分布层系即勘探层位以中-新生界(特别是白垩系和古近系、新近系)为主。
反观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有零星深层探井,但基本没有工业油气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东部油气勘探进入中后期,特别是1984年沙参2井在井深5391m的奥陶系白云岩中获高产油气流,开启了我国西部深层油气勘探的新阶段。在经历十余年的转型摸索后,我国深层油气勘探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规模发展阶段,尤以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成绩*为突出,至21世纪10年代相继发现了塔河、哈拉哈塘、克拉2、龙岗、普光、元坝、克深、安岳、顺南、顺北、满深等大中型深层油气田,并引导和带动了中东部、陆缘海域向深层勘探进军的步伐。
当今国际油气勘探的主要方向是深层、深水、非常规等三大领域,比较而言我国在深层领域无论是勘探投入还是勘探成效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如此,根据2015年全国油气资源构成评价(图1-5),我国深层常规油气资源约671亿t(油气当量),占油气资源总量的34%,但探明率仅13%(油)、10%(气)。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全球深层油气发现主要分布在4500~6000m埋深;而近年来6000~8000m的新发现愈来愈多,其中以我国的表现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16~2020年(“十三五”期间)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的探井90%以上钻至深层和超深层,塔里木盆地钻至超深层的比例甚至达到75%以上。而根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深层-超深层油气藏地质特征、分布规律及目标评价”2021年新的评价结果,深层油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