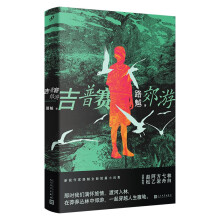曾繁卿是曾祥晖的父亲,曾令维的爷爷。
那天清晨,当酒醉未醒般的太阳,神情恍惚地从曾家铺村后雾气弥漫的树林里露出大半个潮红色脑袋时,曾繁卿的父亲曾庆策就端着那根两尺多长、油光水滑的大烟枪,站在老屋的大门口,边打着哈欠,边朝不远处牛棚里的曾繁卿大声喊道:“繁卿,该去学堂了。隔壁的祥成早就去了。今天你又比他晚了。”
“哎。”曾繁卿稚气地答应一声,将竹篮底部最后一把沾满露水的青草放到木槽里,然后轻轻拍了拍那头老水牛毛茸茸的额头,提着竹篮,像只机灵的小狗一样,弓身从低矮的牛棚里钻了出来。他迈着细小的碎步,很快走到老屋的大门口。他朝刚抽了一口大烟,正闭目养神的父亲看了一眼,随手将竹篮放到大门右手边的青石墩上,接着跨过高大气派的大青石门槛,一路小跑地进到宽敞的屋子里。每天早上,或者从沾满露水的田埂上,或者从波光粼粼的水塘旁,或者从更远处雾气弥漫的鲁湖边,打上满满一竹篮喂牛的青草,已经像每天到学堂里念书一样,成了曾繁卿必不可少的功课。虽然从来没有人安排他做这件事情,但久而久之,不仅曾繁卿自己习惯了,并且所有的人也都习惯了。
不到两分钟,曾繁卿右手提着一只小巧的小木箱从屋子里出来了。小木箱是去年夏天曾繁卿开始到学堂里念书前,父亲特意找了村里的老木匠宪财叔爹,用质地细腻并且不会生出裂纹的桑树做成的。洁白光滑的木板上涂了层似有似无的桐油,太阳光下闪烁着一抹神秘的光泽,看上去像一件不可多得的宝贝。曾祥成的木箱也是宪财叔爹做的,只不过是用最平常的槐树做的,并且按曾祥成的父亲曾繁盛的要求,通体涂成了暗红色,与平常人家用来装杂物的木箱并无大的差别。
“送给先生的米带上了吗?”父亲眯缝着眼睛,问道。
“带了。放在书箱里。”
“钱呢?”
“拿了,揣在荷包里。”
曾繁卿清脆地答应着,像一缕轻风一样从父亲的身边走过。然后,往左边一拐,蹦蹦跳跳地踏上那条穿村而过、用一块块碗口大小青石块铺面的小路。到冬天他才满七岁,远没到发育的年龄,由于个子太小,也过于瘦弱,从背后看去,提在右手的小木箱过于沉重,使他纤细的身子明显往右倾斜。
小路像条菜花蛇一样,曲里拐弯地穿村而过,到了村后的树林边缘,就完全没了踪迹。在一连半个多月的春雨浸润下,与青石铺面的小路相连接的村外那条土路早就没了以前的模样,除了深浅不一的牛蹄印外,再就是大大小小盛满浊黄色泥水的水坑。曾繁卿像玩杂耍一样,有时侧过身子,有时攒足力气往前一跃,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讨厌的水坑,但还没走上一百米远,脚上的黑色布鞋就差不多被泥水浸湿透了。他犹豫了一下,蹲下身子,将脚下的布鞋脱下来,提在左手上,继续往前走。早春的泥水仍然冰凉,但是,他不再在乎脚下的那些水坑了,行走的速度也一下快了许多。
走出村后那片茂密的树林,就可以看到那片水田对面的敖家湾了。在黛青色的雾气中,那一大片黑灰色的房子隐隐约约像悬在半空中一样,有如幻境中的仙山楼阁。这个时候,只有那棵高大的刺槐树显得最为醒目,像一大团深绿色的云彩一样,轻轻地飘浮在房子的上面。那两颗喜鹊蛋已经孵出小喜鹊了吗?昨天中午,在曾祥成的一再怂恿下,曾繁卿趁先生上茅房的机会,像猴子一样飞快地爬到槐树上。从散发出刺鼻臭味的鸟窝边沿,他清楚地看到那两颗散发出淡淡光泽的青灰色喜鹊蛋。从树上爬下来后,他兴奋地告诉曾祥成,就这两天,小喜鹊就会破壳而出。
“真的吗?”曾祥成兴奋得咧开缺了牙的嘴巴。这段时间他正换牙,由于羞于让人看到缺失的牙齿,一直将嘴唇抿得紧紧的,所以在曾繁卿的脑子里留下一个奇怪的模样。
接下来,曾繁卿小心地走上那条有三百多米长的田埂。田埂呈弧形,两边的水田已经蓄上了齐膝深的水,松软的泥土以及泥土表面无数板栗大小的田螺,在清澈的水底清晰可见。更远处的一块水田里,庆喜叔光着双腿,大声吆喝着,驱使自己家那头最壮实的大牯牛犁田。庆喜叔的儿子来旺提着一只竹篓,同样光着双腿,紧跟在大牯牛和他父亲后面,紧张地盯着被犁铧翻起的泥土,生怕遗漏一条在泥水中挣扎的泥鳅或者鳝鱼。来旺虽然比曾繁卿还小半岁,但他捉鱼摸虾的能力始终让曾繁卿自叹弗如。
“上学呀!”庆喜叔看到了曾繁卿,大着嗓子与他打招呼。
“是呀。”曾繁卿答应着,很快将庆喜叔和他儿子来旺以及那头大牯牛丢在了身后。但他的脑子里始终抹不去来旺那可怜巴巴的眼神。这主要缘于去年曾繁卿和曾祥成开始到敖家湾的学堂里念书后,来旺也吵着要去念书,结果书没念成不说,还被他那长着一双三角眼、喜欢贪小便宜的父亲狠狠揍了一顿。自那时开始,曾繁卿才明白在曾家铺,不是任何人都念得起书的。
曾繁卿走进学堂里时,先生正坐在大门旁边的那把高大的太师椅上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烟。曾繁卿将沾满泥巴的双脚并拢,小心翼翼地朝先生鞠了一躬,又走到案几下面,朝万世师尊的孔子牌位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然后才走到靠近曾祥成的座位上坐好。
“米和学费钱带来了吗?”先生仍捧着水烟壶,瓮声瓮气地问道。
“带来了。”曾繁卿答应着,急忙将小木箱打开,将黑色粗布做的米袋提起,放进先生身后的一只已经堆满大小米袋的竹筐里,又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小心地放到先生已经伸出来的右手掌里。
先生双眼若睁若闭,缓缓地将银圆放进嘴里,用仅剩的几颗黑牙轻轻咬了咬。接着,又用拇指和食指拈住银圆,嘬起干瘪的嘴唇,使劲往银圆上吹一口气,然后忙不迭地将发出嗡嗡声响的银圆贴紧蜡黄的耳朵,仔细倾听起来。直到这时,先生一直紧绷着的瘦脸才完全舒展开,下巴上那撮已经花白的胡子也霎时充满了生气,开始轻轻抖动起来。
将银圆揣进长衫里面的荷包以后,先生扶着膝盖慢慢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又将垂在背后的那根又细又长的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然后左手小心地端着水烟壶,右手夸张地从侧面平伸出去,伸了个十分惬意的懒腰。接着,先生好像若有所悟,用感慨的语气说:“银圆确实是个好东西,但印在银圆上的袁大头却十足是个不忠不孝之徒。”
曾繁卿虽然知道大家之所以将银圆称作袁大头,主要是缘于银圆上印着的那个胖乎乎的老头的头像,但这胖老头到底是谁,他确实不知道。所以,他仍傻傻地站在先生的面前,仰着头,用困惑的眼神看着先生。
“回座位上去吧。”先生朝曾繁卿摆了摆手,慢慢踱到案几那儿。在将水烟壶放到案几上后,他缓缓转过身,倒背着双后,对曾繁卿以及其他八个大瞪着双眼的小男孩说道:“今天,我就从这袁大头说起,给你们讲讲祖宗留传下来的悌孝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
……
七岁不到的曾繁卿每天都重复着以上的生活。这是他的父亲曾庆策对他严格要求的结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