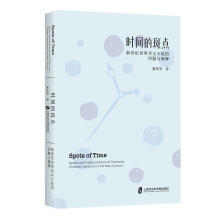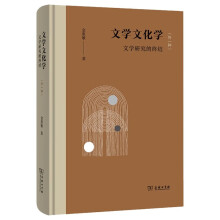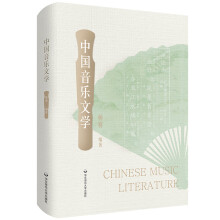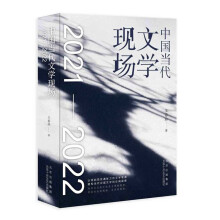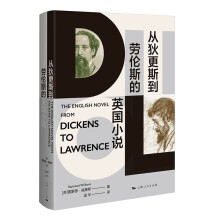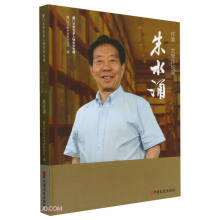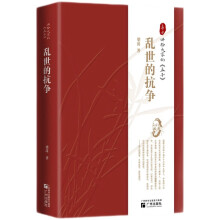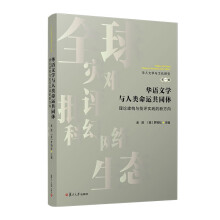《清代才学小说考论》:
从儒家学术发展的内在线索讨论了明末清初至清代中叶学术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演化后,不妨再从清代才学小说周围的文化生态,即政治、社会与地域等因素来看清代学风从清初至中叶的构成理路。
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覆灭,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入主中原。国家兴亡与政权更迭,无疑会构成清初士人生活最显豁的生存特征,而这一定会折射到学术与学风上来。杜桂萍先生认为:“清初的学风既具有历史的延续性,遵循其内在的理路,但同时也是朝野上下通力合作的结果。在表述一种普遍的道德意义与对秩序的忧虑态度时,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士人与政体达成过如此默契的一致。”对清初的学风进行此种框架式的分析无疑是十分深刻的。笔者看来,这种带有“朝野上下通力合作”特质的学风在清代中叶——乾嘉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实在。
伴随着清初三大家对经世致用学风的提倡,兴起了实学思潮。这种实学思潮随着清初对理学的推重而发展,随着清中叶乾嘉汉学的兴起而达到高峰。
在明末,王学末端的空疏学风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士人的关注。这种关注又因为明末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种种内忧外患的矛盾和中外文化交流逐渐深入的大背景,从而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东林、复社士人以卫道、辟佛、尊孔、读经为门径,来批判王学的空疏弊端,在由虚而实的学风转变中,无疑具有拓荒之功。
清初至清代中叶,面对着空前的时代变革以及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尤其是明朝的覆亡和清朝的遽然兴起,更多的士人开始了深刻的反省。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云:“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陆陇其《上汤潜庵先生书》认为:“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③陆陇其甚至还将明代的灭亡归咎于王学。他在《学术辨》中说:“明之天下不亡于盗寇,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盗寇、朋党之祸也。”这种将国家兴亡与学风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未免有夸大理论的社会功用之嫌,但由于学者的出发点是致力于寻找切实可行的救世途径,所以是可以获得理解的。
世所公认,汉学才是清代学术之主体。冯友兰分析说:“所谓汉学家者,以为宋明道学家所讲之经学,乃混有佛老见解者。故欲知孔孟圣贤之道之真意义,则须求之于汉人之经说。”这是因为“两汉经学,所以当遵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乾嘉考据为其典型代表。清代汉学,其开山鼻祖当然是顾炎武,随后是阎若璩、吴渭奠基,到了惠栋公开打出旗号,一代学术才正式确立。考据学内部也是学派林立,有惠栋之吴派和戴震之皖派以及稍后的扬州学派等。吴派弃宋宗汉,专攻汉学,认为:“《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用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戴震学识渊博,识断精审,可谓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他对惠栋吴派采取的是既推崇其由文字、音韵、结构、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又不墨守惠栋所创汉学成规。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也;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阮元、汪中、焦循、凌廷堪等,皆为戴震后学,他们继承戴学,对吴派也不拒斥,能够本着兼容并包的精神吸纳两家之长,从而形成求同存异、不墨守门户的学术态度。扬州学派的学术贡献,充实并完善了清代汉学,正是经过吴、皖两派及扬州学派的共同努力,乾嘉考据之风才大盛,汉学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一时四海之内,“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矣”。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对学者最具吸引力的学问。扬州学派的领袖阮元对此曾进行总结,其文云:“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