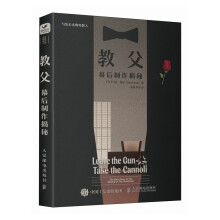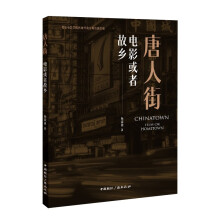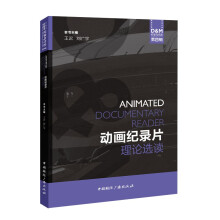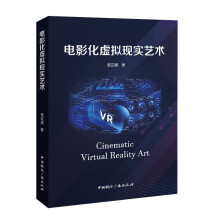《中国喜剧发展研究(1978-2018)》:
一、偏重形式的戏剧观论争
我国戏剧从新文化运动之时,就借用并仿效易卜生“社会问题剧”模式,其创作主潮是现实主义的;在表演上,20世纪30-40年代又引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提出了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看齐的口号,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被推广运用到整个话剧界,成为我国唯一的演剧模式。几十年来,我国戏剧舞台上的主流戏剧就是:剧作内容上以“社会问题”为核心,舞台上追求生活“幻觉”般的表演方式。长期以来,这种单一的戏剧模式一直笼罩整个戏剧界,创作视野越来越狭隘,表演方式越来越僵化。面对这一问题,戏剧界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展开了一场长达8年的关于“戏剧观”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是难以避免的,它既是20世纪80年代戏剧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催发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为何会提出戏剧观的问题而引发大家关注?当然有其历史渊源。
黄佐临1962年3月在座谈会上做了《漫谈“戏剧观”》的发言,“提出了‘戏剧观’这个理论概念”①。针对当时戏剧危机和单一狭隘的戏剧观念、舞台演出模式的僵化形态,他围绕世界上三大表演体系的代表人物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的戏剧观进行了对比,期望找到三者之间的异同点,并探寻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可否彼此借鉴融合、推陈出新的情况,以便能改观我国当时只认定一种戏剧观的狭隘视野,这是黄佐临引入“戏剧观”这一戏剧理论的意图所在。他进一步通过三者跟“第四堵墙”的关系指明了三种戏剧观的根本区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视“第四堵墙”,布莱希特立足如何推倒它,而梅兰芳这里,根本不存在这堵墙。在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区别之后,他又语重心长地提醒戏剧界的同仁要突破之前单一的戏剧观,放眼世界,大胆尝试各种戏剧表现手段与方式,以解决创作形式单一的问题,走出戏剧危机。在喜剧界寸步难行的重重危机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来势汹汹之下,喜剧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喜剧必须在继承戏曲表现手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戏剧技法,以革新传统喜剧。而在本次大讨论中,由于发起者黄佐临是围绕与“第四堵墙”之间的关系辨识来区分三种戏剧观的,所以喜剧界也是围绕“第四堵墙”理论及其与之相关的“写实/写意”“幻觉/非幻觉”和“假定性”等戏剧表现形式进行研讨的,这就使这次讨论偏重于对戏剧形式的探讨。这种倾向对喜剧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有两方面:一方面伴随着对喜剧形式的探讨,我国话剧舞台的喜剧形式包罗万象,各种形式的喜剧百花齐放;另一方面正因为过于看重形式,导致喜剧创作人文内涵与戏剧精神缺失,对剧本创作敷衍,对戏剧结构、戏剧冲突和戏剧情境漠视。因而,当时这种偏重喜剧形式的倾向对喜剧发展的影响一直存在,目前喜剧整体创作水平低下,偏重对各种形式的创新与喜剧笑点的挖掘,而忽略喜剧人文精神与喜剧内涵,内容与形式没有达到和谐统一。
喜剧探索实践紧密围绕“戏剧观”争论而行进,其形式探索的实质主要表现为对“三一律”的僭越与对传统镜框式舞台局限的突破。
“三一律”是戏剧结构理论之一,是一种关于戏剧结构的规则,主要是指戏剧创作必须遵循动作(事件)、地点、时间完整一致的规则,又称“三整一律”。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以古希腊、古罗马戏剧为楷模,为恢复其严谨、整饬的风格,在艺术形式上以遵守“三一律”为主要标志,此规则在欧洲剧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
展开